凌晨三点,林薇摘下耳机,耳道里还残留着客户“老板”油腻的笑声。电脑屏幕上,最后一条转账记录闪烁——888元,附言是“妹妹明天见”。她扯了扯嘴角,想笑,却只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叹息。这已经是本周第七个提出“线下见面”的客户了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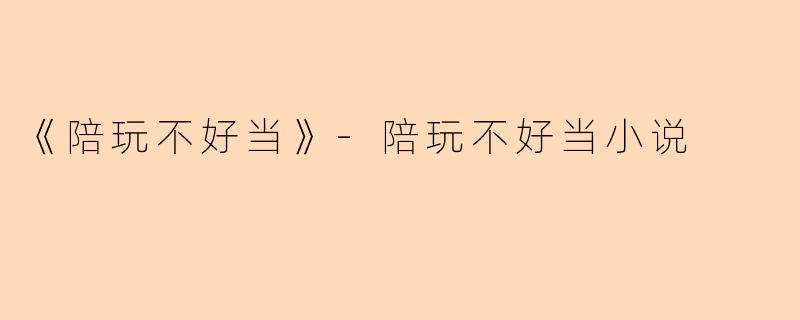
入行时,林薇以为这行不过是打打游戏、唱唱歌。她游戏打得好,声音也算清甜,在陪玩平台挂出资料卡后,订单很快涌来。起初是正常的游戏对局,接着是要求连麦闲聊,再后来,私信里开始出现暧昧不明的试探。“老板”们用金钱铺路,一点点试探着边界。她学会了在撒娇卖萌和保持距离之间走钢丝,把拒绝包装成俏皮的推脱,把不适掩饰成网络延迟般的沉默。
真正让她感到刺骨的,是上周的订单。客户ID叫“过客”,点了最贵的套餐,却一整晚只要求她反复念一段毫无意义的台词。他的呼吸声透过麦克风传来,平稳得令人心慌。结束后,“过客”发来一句:“你声音很像她,可惜你不是。”随即拉黑。那笔高昂的费用,像一枚冰冷的勋章,钉在了她的耻辱柱上。她意识到,自己贩卖的从来不是技术或时间,而是某种情绪价值的幻影,是孤独者临时的情感止痛剂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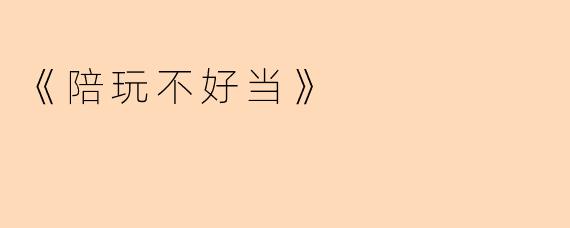
白天,她是沉默寡言的大学女生;夜晚,她是声音甜腻的“薇薇酱”。两种人生在黄昏时分交割,界限却日益模糊。有次母亲突然视频,她手忙脚切换掉变声软件,用本音仓促应答,母亲疑惑地问:“薇薇,你嗓子怎么哑了?”她看着镜中自己还未卸掉的浓妆,突然一阵反胃。
这个行业光鲜的流水背后,是不断被物化与自我物化的拉锯。她必须记住每个“老板”的喜好,扮演他们需要的角色——清纯学妹、知心姐姐、傲娇大小姐。情绪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,而真实的喜怒哀乐,却要在下麦后才会缓慢反噬。同行群里,有人炫耀日入过万,也有人突然消失,只留下关于“跟老板走了”的暧昧传闻。每个人都像在薄冰上跳舞,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欲望寒潭。
今晚最后一个订单,是个新手。男孩声音青涩,输游戏后连连道歉。她忽然想起最初的自己,那句“没关系,我们再来”说得格外真诚。结束时,男孩犹豫着问:“姐姐,你……做这个开心吗?”林薇愣住了。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,明明灭灭。她深吸一口气,敲下职业性的回复:“开心呀,能陪你玩就很开心呢。”
发送成功。她关掉电脑,房间陷入黑暗。窗外,城市灯火通明,无数相似的窗口里,是否也有相似的灵魂,正在贩卖或购买着短暂的慰藉?她揉了揉僵硬的脸颊,知道明天太阳升起后,“薇薇酱”又将准时上线。只是耳机戴久了,总会有些疼,那种疼细细密密的,仿佛要钻进骨头缝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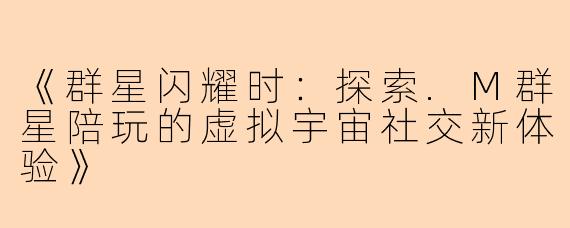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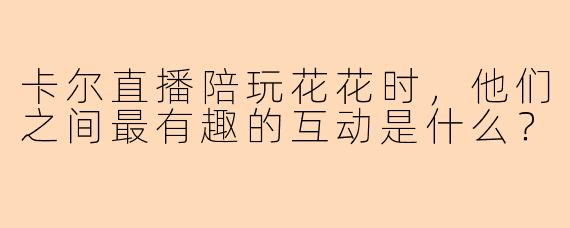

![[用户想了解关于“点陪玩”的什么具体信息?例如是平台介绍、服务流程、消费价格、还是如何成为陪玩师?]](https://www.fcyhdmw.com/img/2026/01/点陪玩之
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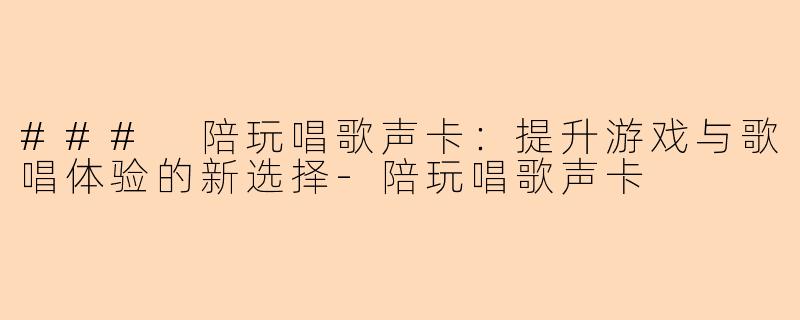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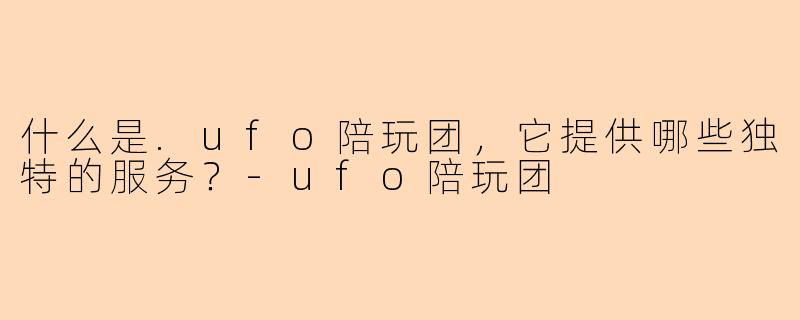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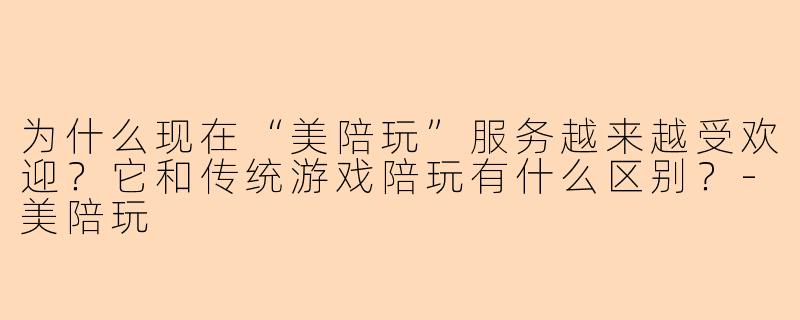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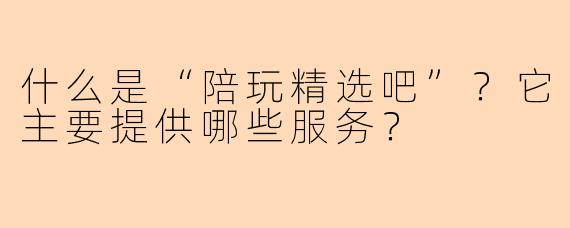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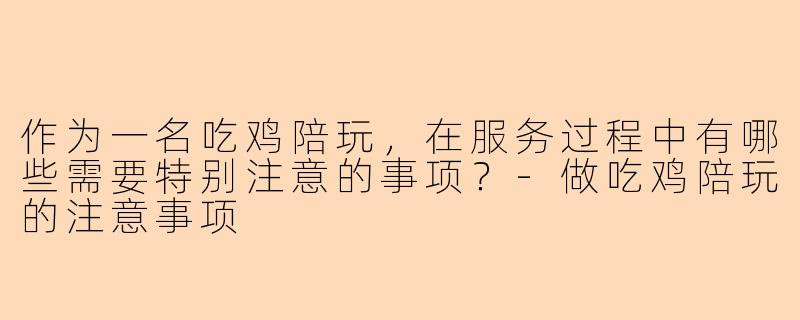
![[请问在.cp陪玩试音中,你们主要考察哪些方面的能力?]](https://www.fcyhdmw.com/img/2026/01/5093eb214a0ff25d76f4b394351502ed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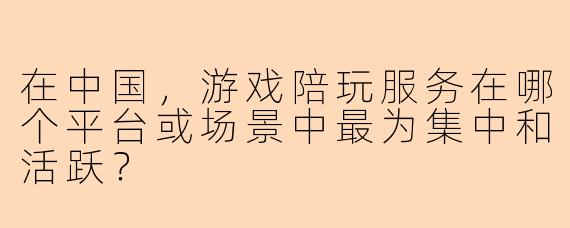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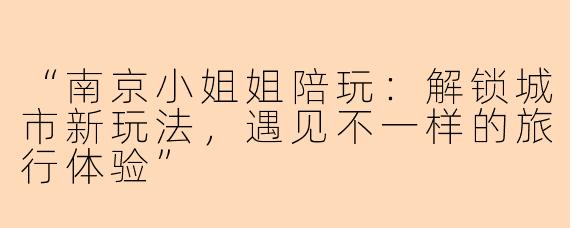
![[关于伴伴陪玩1997这款应用,它主要提供哪些服务?]](https://www.fcyhdmw.com/img/2026/02/伴伴陪玩1997
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