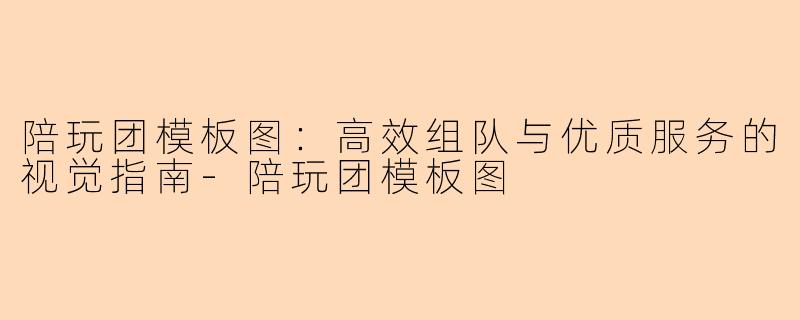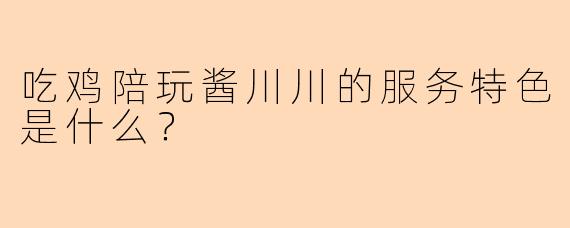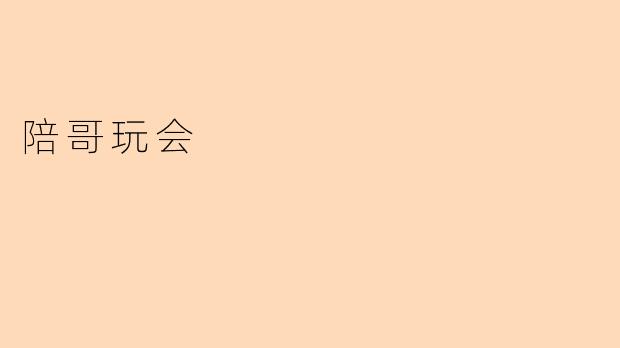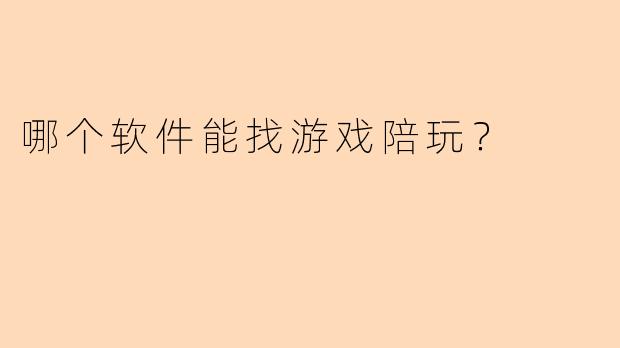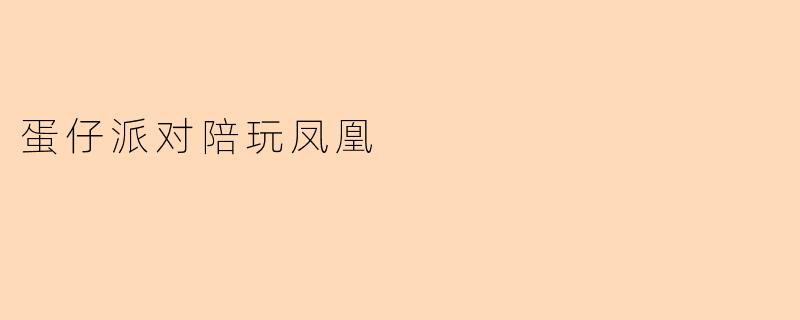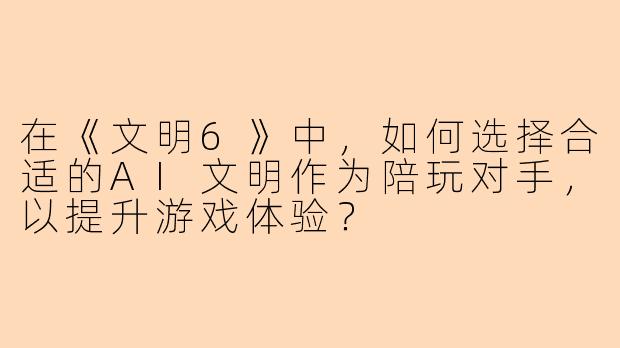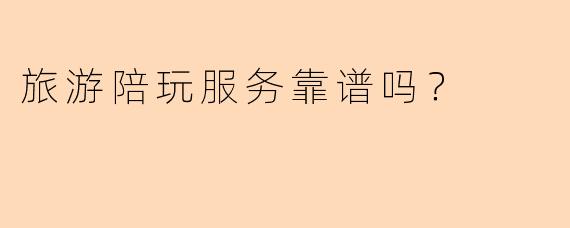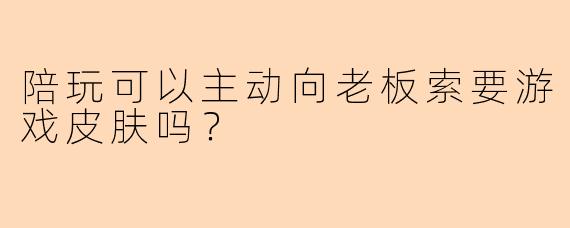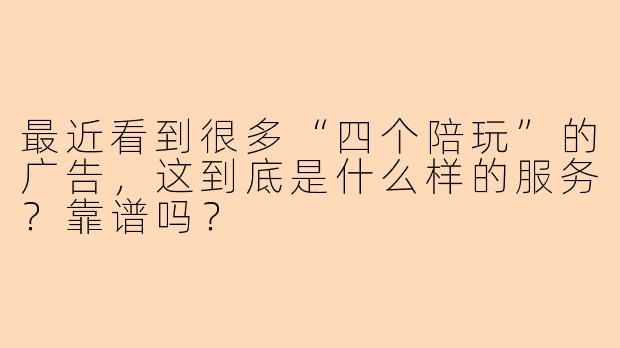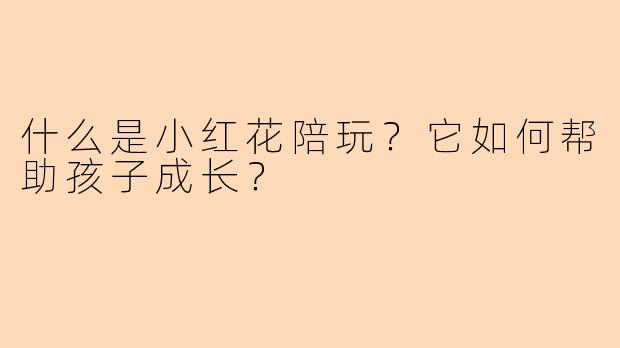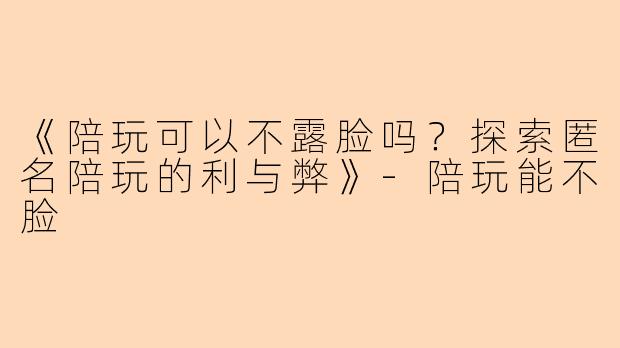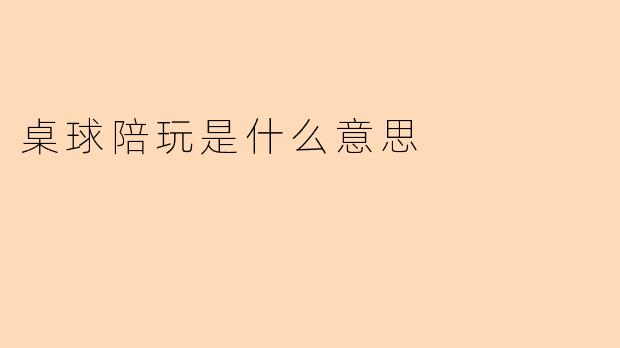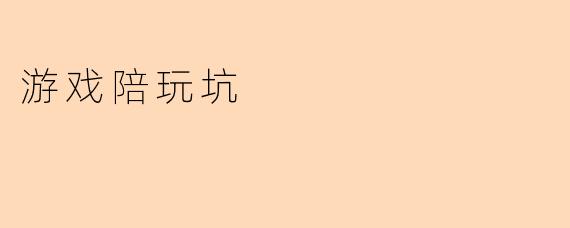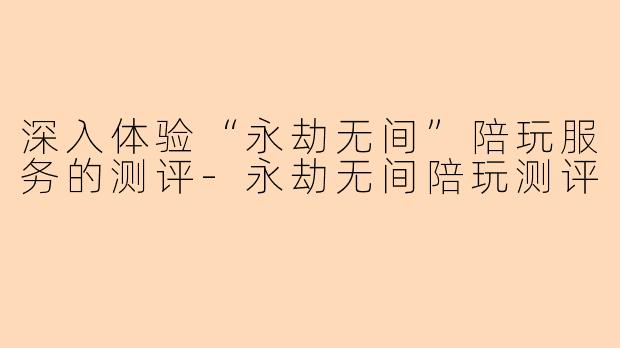青石板路在雨后泛着光,蜿蜒穿过白墙黛瓦的巷弄。琵琶声从某扇雕花木窗里飘出来,像是时光深处的叹息。这是苏州寻常的午后,而我,是这座城里一个不那么寻常的陪玩者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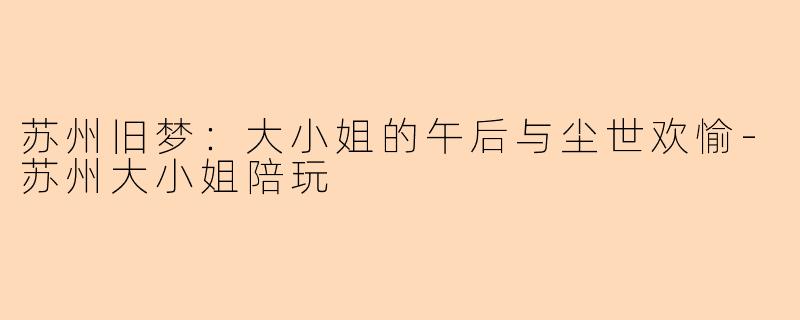
客人们唤我“大小姐”,半是戏谑,半是因着我身上那点所谓的“苏州味道”。我家在这座城住了几代,谈不上大富大贵,但老辈人总还守着些旧式规矩。我能泡一手不错的碧螺春,认得几种失传的苏绣针法,甚至能磕磕绊绊地弹半曲《梅花三弄》。这些在如今看来无用的技艺,却成了我陪伴四方来客的凭藉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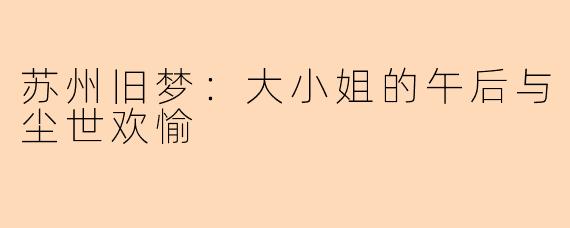
陪伴,从不是简单的向导。它更像是一场精心又不着痕迹的演出,而我,是那个引领他人短暂潜入苏州骨血里的角色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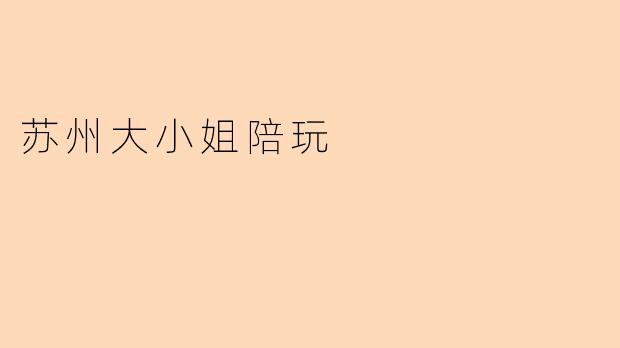
我们会在平江路的评弹馆里消磨一个下午。吴侬软语咿咿呀呀,唱的是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。我轻声为客人翻译着唱词,讲那《玉蜻蜓》里命运的无奈,讲《钗头凤》中错过的深情。茶水氤氲的热气里,他们的眼神会渐渐迷离,仿佛真的触碰到了几百年前那座温润又伤感的城池。
也会去艺圃或耦园,那些不那么喧闹的园子。在逼仄假山与一池碧水构成的天地里,我告诉他们,为何窗要开在这个角度,为何石头要垒成那个形状——那不是堆砌的风景,是古代造园者试图在一方天地里,容纳整个宇宙的微缩哲学。我们坐在水榭里,看光影在花墙上移动,时间慢得如同凝固。偶尔,我会带来一套素雅的茶具,行云流水地演示功夫茶,那时,连风都似乎变得轻柔,怕惊扰了这份仪式感。
当然,也有活泼的时候。带他们去山塘街寻找最地道的生煎,看师傅如何将一锅馒头舞动得滋滋作响;或是深夜钻进一家隐于市井的书场,听一段市井气息浓郁的苏州笑话,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时,“大小姐”的壳子便暂时卸下,我成了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一个投缘的、识途的本地朋友。
夜色中的七里山塘,红灯高挂,倒映在水中,碎成一片流动的锦绣。一位北方的客人曾在此对我说:“跟你游苏州,不像旅游,倒像在读一首活过来的、立体的诗。”
我笑了笑,没有回答。 我只是这座千年古城的一个注脚,一个用陪伴作针、以时光为线,为他们浅浅绣下一段苏式记忆的引路人。当曲终人散,他们带着对苏州的“感觉”离去,而我的午后,依旧在琵琶声里,等待着下一段尘世欢愉的相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