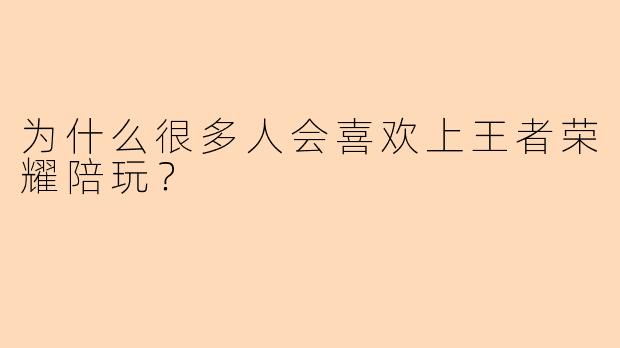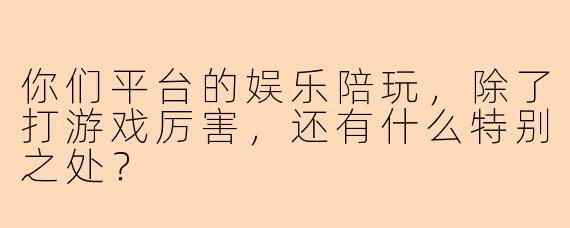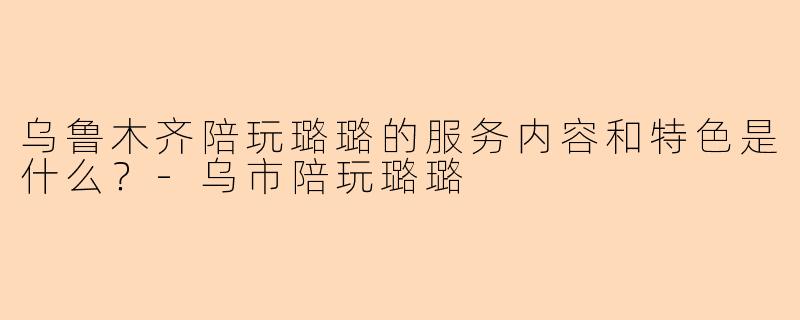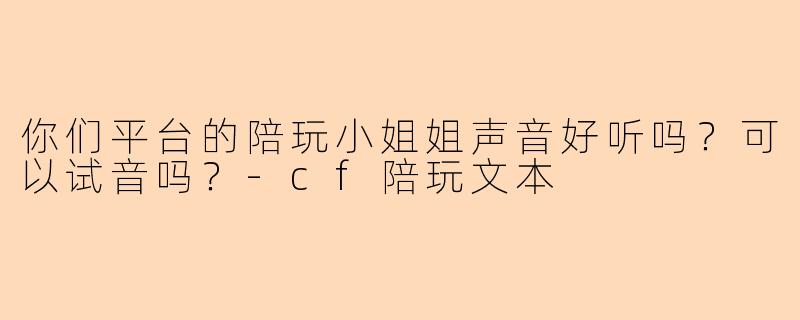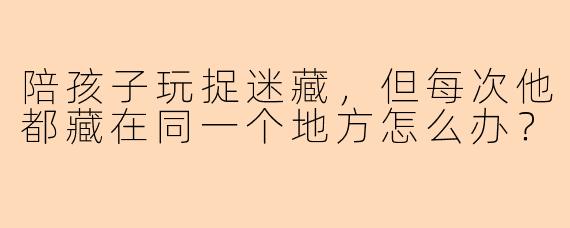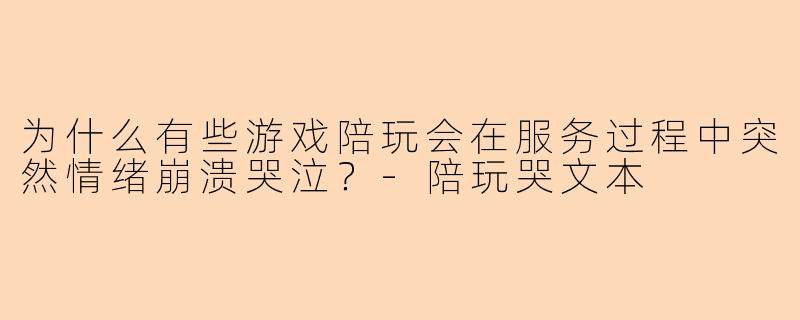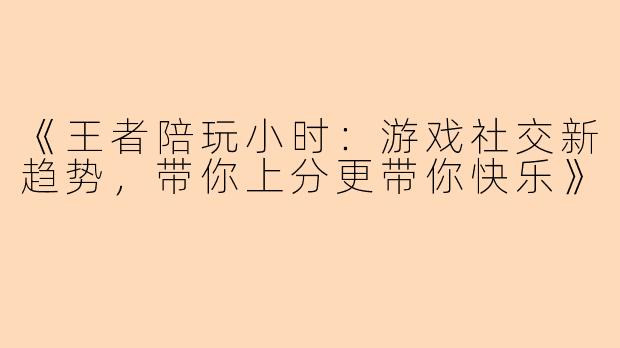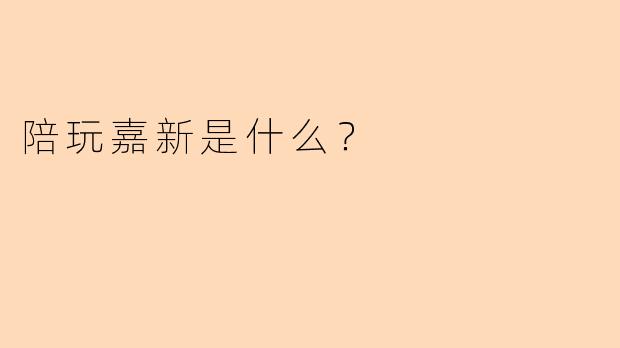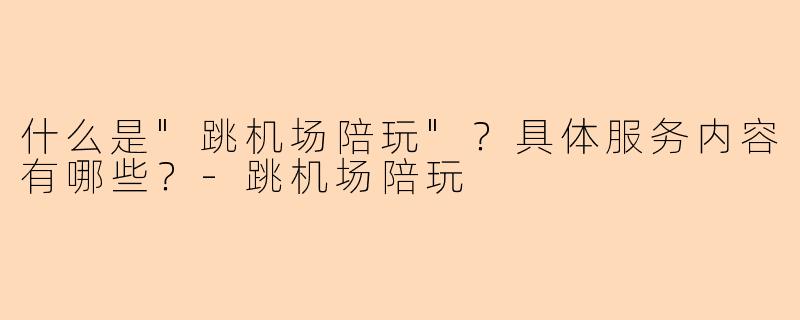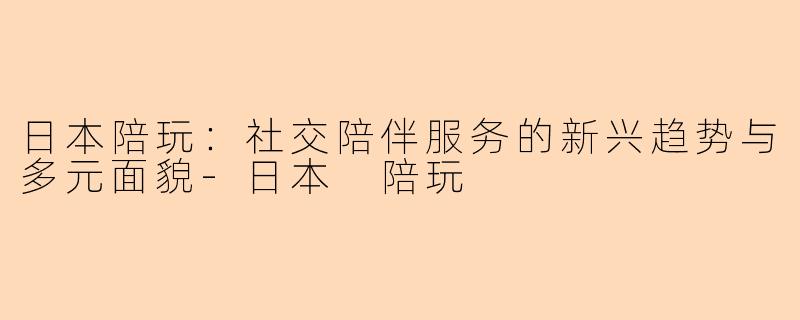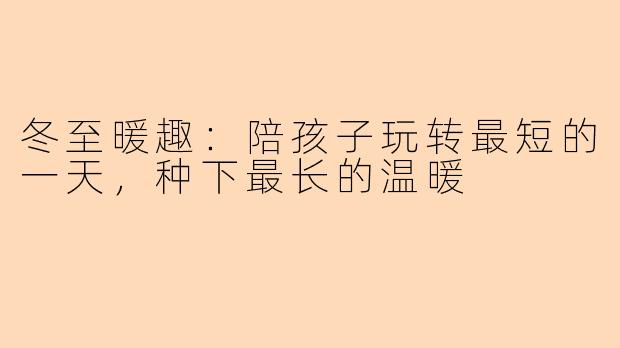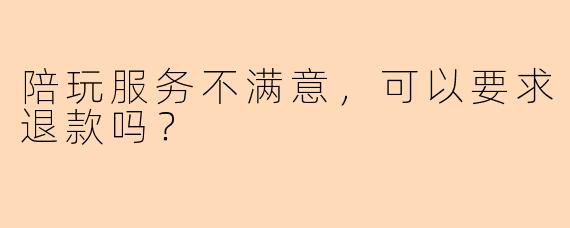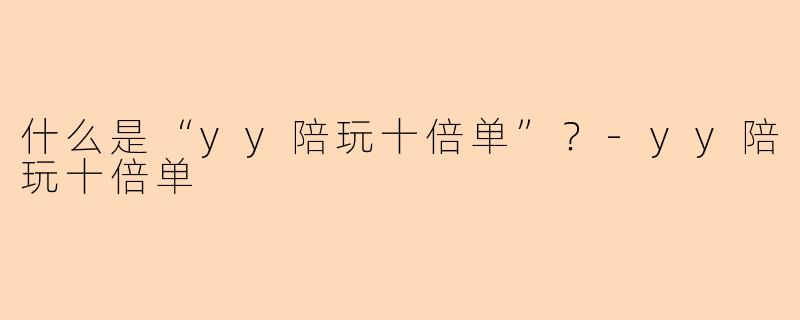腊月二十九的傍晚,我站在异乡的落地窗前,看着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,手机屏幕上是母亲刚发来的消息:“年夜饭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八宝饭。”指尖在键盘上停留许久,最终只回了一句:“妈,今年项目赶工,不回来了。”
这已是我连续第三年缺席家乡的团圆饭。但这一次的春节,却因一个意外的承诺而变得不同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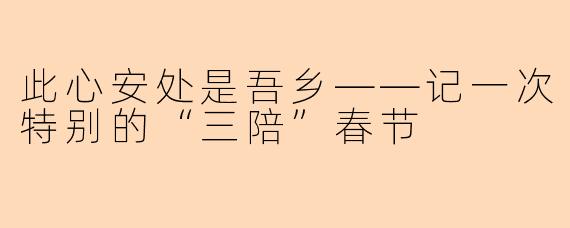
“李姐,您儿子也不回来吗?”小区物业的王阿姨在采购年货时与我偶遇,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同样的落寞。她的独子远在非洲援建,已是第五个春节未曾归家。那一刻,一个念头突然涌现:“王阿姨,要不……今年我陪您过年?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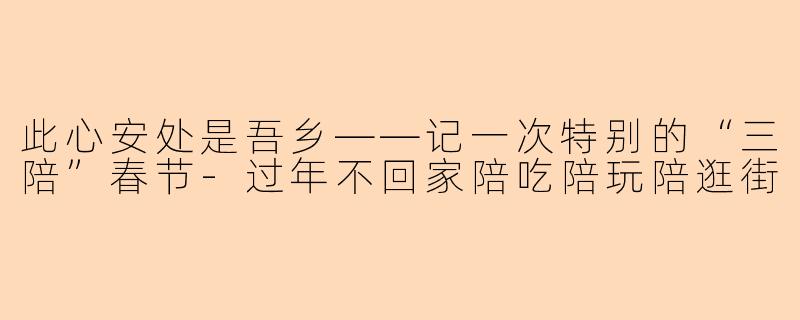
于是,一个特殊的“三陪”春节拉开了序幕。
大年三十清晨,我系上围裙,在王阿姨家那间充满八十年代气息的厨房里,开始复刻记忆中的年味。王阿姨翻出泛黄的食谱,指着“糖醋排骨”那一页:“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。”油锅滋滋作响,当琥珀色的排骨出锅时,她忽然轻声说:“这味道,有七分像了。”窗外飘着南国罕见的细雪,厨房里的蒸汽模糊了窗玻璃,也模糊了我们的眼眶。
年初一的商业街张灯结彩,我挽着王阿姨的胳膊走过一家家店铺。在年轻人聚集的奶茶店前,她好奇地张望:“现在的孩子都爱喝这个?”两杯热奶茶下肚,她像个孩子般举着空杯让我拍照:“发给我儿子看看,我也时髦了一回。”路过童装店时,她驻足良久,最终买下一件红色小棉袄:“等我孙子回来穿,应该正合适。”那件棉袄被她仔细叠好,放进了早已装满礼物的衣柜深处。
最触动我的,是年初三的午后。我们坐在社区活动中心,周围是七八位同样子女未归的老人。刘爷爷拿出二胡,咿咿呀呀地拉起了《良宵》。琴声有些生涩,但所有人都安静地听着。王阿姨悄悄告诉我,刘爷爷的儿子是驻守边疆的军人,上次回来还是三年前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我们陪伴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位长辈,而是在这个高速流动的时代里,所有守望的灯火。
元宵节那晚,我和王阿姨一起煮汤圆。视频铃声突然响起,屏幕那头是她儿子黝黑的笑脸,背后是撒哈拉的星空。“妈!项目提前完工了!我买了下周末的机票!”王阿姨的手微微颤抖,汤勺落入锅中,溅起小小的水花。
送别时,她紧紧握着我的手:“闺女,谢谢你让我这个年过得……不那么像在等待。”回到冷清了一周的出租屋,我忽然收到母亲发来的照片——餐桌中央,赫然摆着一碗糖醋排骨。母亲留言:“跟你视频里做的挺像吧?我跟你爸学着做的。”
窗外,不知谁家放起了新春的最后一串鞭炮。在这个没有回到地理意义上故乡的春节,我却意外地抵达了“年”最本质的深处:所谓团圆,从来不只是血缘的相聚,而是心灵被温柔照亮的时刻。我们这些漂泊的游子,或许正是在一次次给予温暖的过程中,治愈了自己的乡愁。
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。当陪伴成为双向的奔赴,每一个他乡,都可能生长出故乡的根系;每一次短暂的相遇,都在延展着“家”的边界。这个春节,我没有回家,却找到了更多回家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