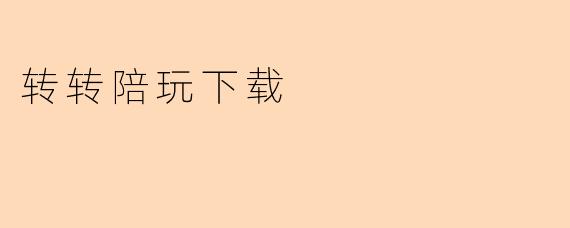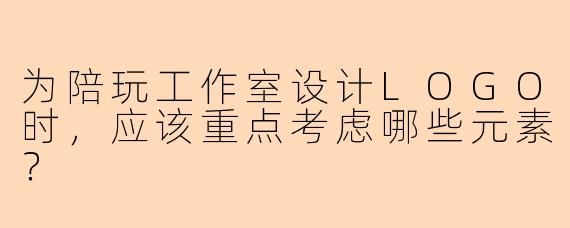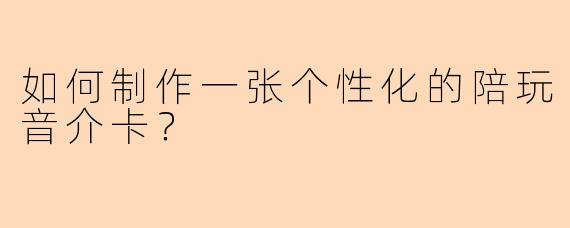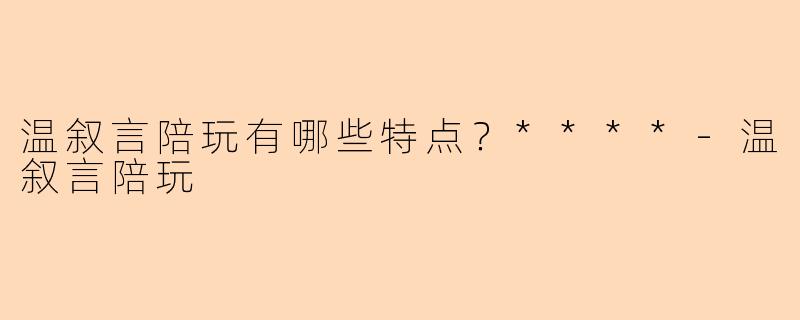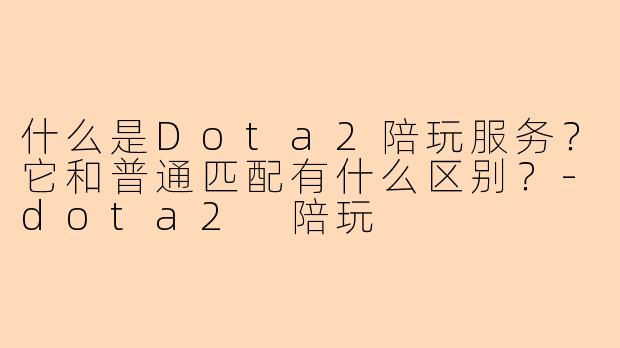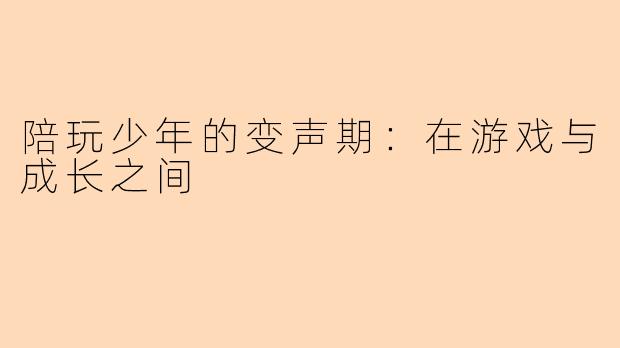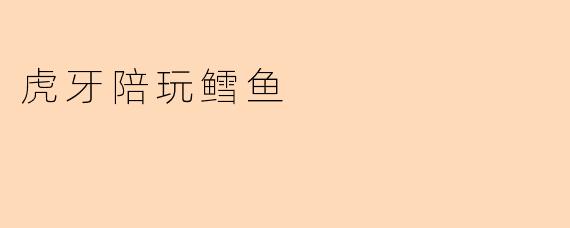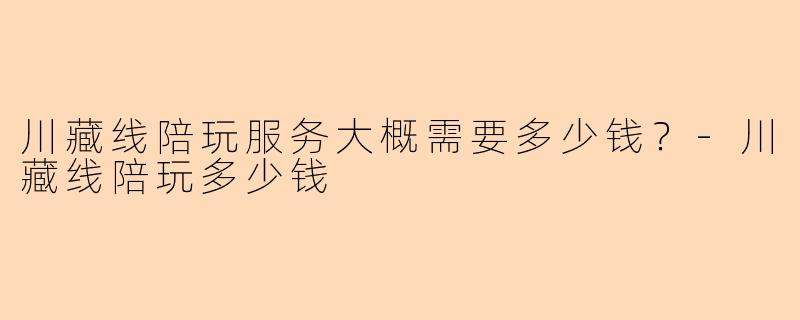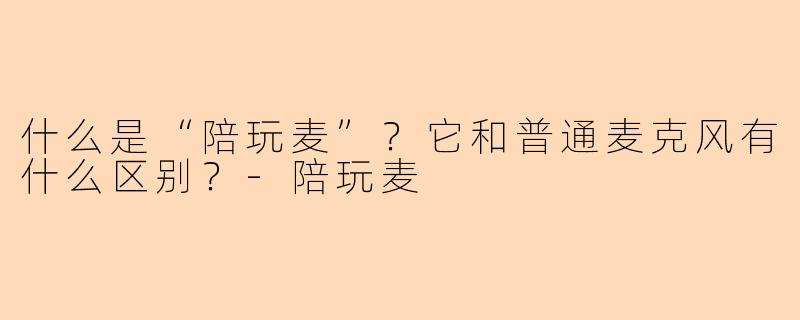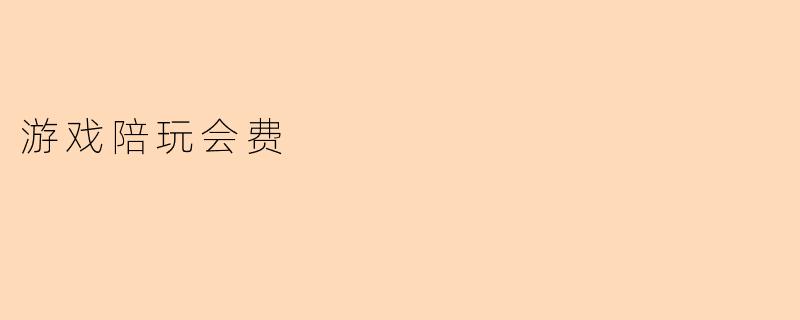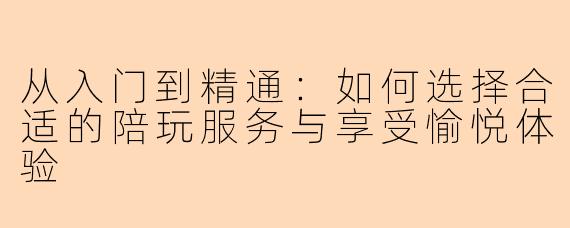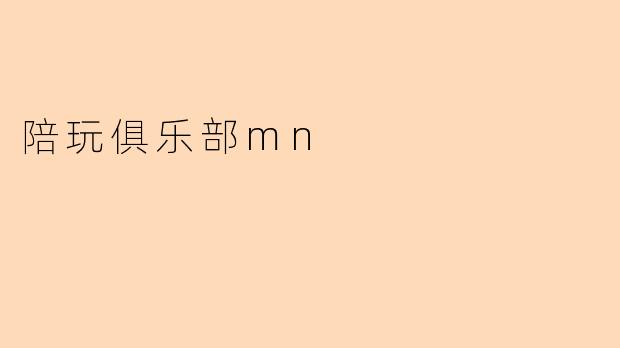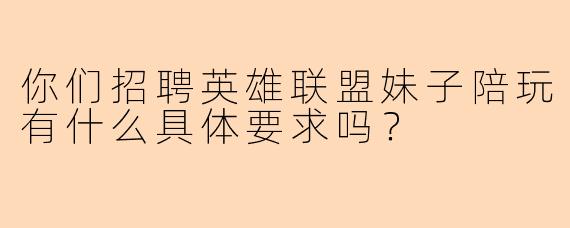在无数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看着孩子兴高采烈地摆弄积木或玩具车,内心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疲惫。是的,我讨厌陪孩子玩。这句话说出来时,我几乎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审判意味——在这个推崇“高质量陪伴”的时代,承认这一点仿佛成了一种罪过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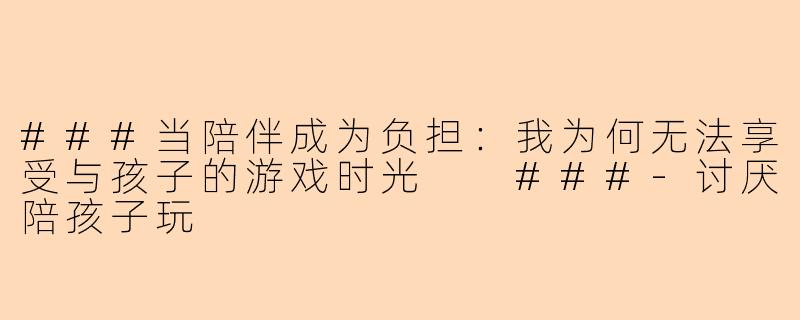
起初,我也曾努力扮演那个充满耐心的父母。我会盘腿坐在地板上,堆砌那些五彩斑斓的积木,假装对“过家家”的故事线充满兴趣。但不到十分钟,我的思绪就开始飘散:未回复的工作邮件、待收拾的厨房、甚至只是渴望片刻独处的自己。孩子的笑声变得刺耳,那些重复的游戏规则让我昏昏欲睡。更可怕的是,我开始计算时间,像等待刑满释放的囚徒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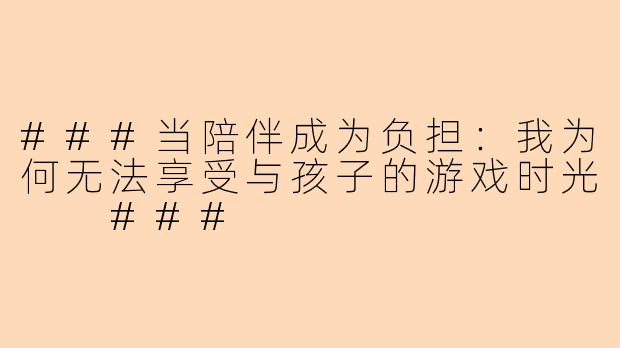
这不是因为我不爱我的孩子。恰恰相反,正是这份爱让我的愧疚感如此沉重。我试过说服自己:陪伴的质量胜过数量。但当我第三次拼错同一块拼图,当我不耐烦地打断孩子的奇思妙想时,所谓的“高质量陪伴”成了最讽刺的谎言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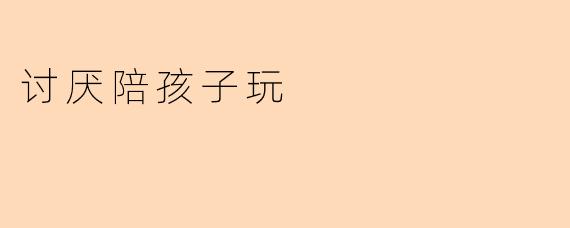
心理学家说,成年人与儿童的大脑运作方式本就不同。孩子通过重复和探索来认识世界,而成年人早已习惯了目标导向的思维。当我们被迫沉浸在看似毫无意义的游戏中时,那种认知失调会引发真实的生理不适。这不仅是心理上的抗拒,更是大脑在发出求救信号。
我逐渐明白,问题不在于“讨厌陪玩”本身,而在于我们如何定义“陪伴”。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幼稚的游戏来证明爱?为什么不能把日常互动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陪伴?一起烘焙时面粉飞扬的厨房,散步时关于云朵形状的讨论,甚至只是并肩坐着各自看书——这些难道不都是珍贵的共处时光吗?
如今,我学会了与这份“讨厌”和平共处。我会坦诚地告诉孩子:“妈妈现在需要休息半小时,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公园。”我也会找到双方都能享受的活动,比如一起种花或做简单的手工。界限分明之后,那些刻意陪伴的时刻反而变得轻松起来。
也许,我们该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本质。爱不是一场必须按照固定剧本演出的戏,而是允许彼此真实存在的勇气。当我放下“完美父母”的包袱,承认自己的局限,反而在孩子眼中看到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。
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诚实的父母,而不是更多完美的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