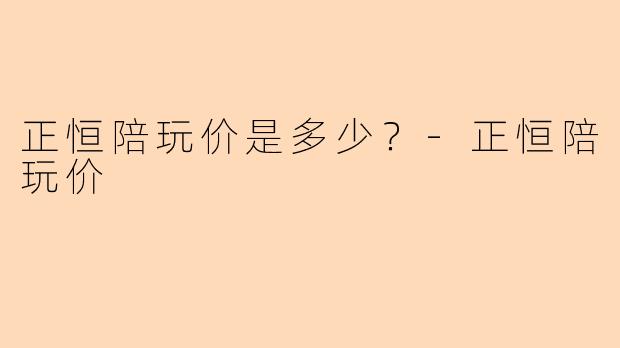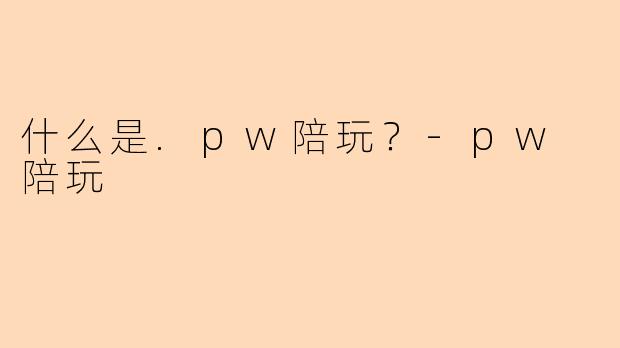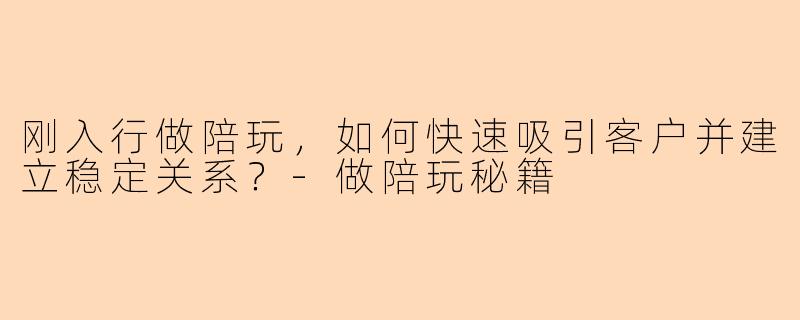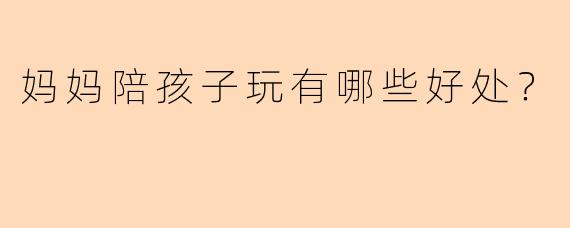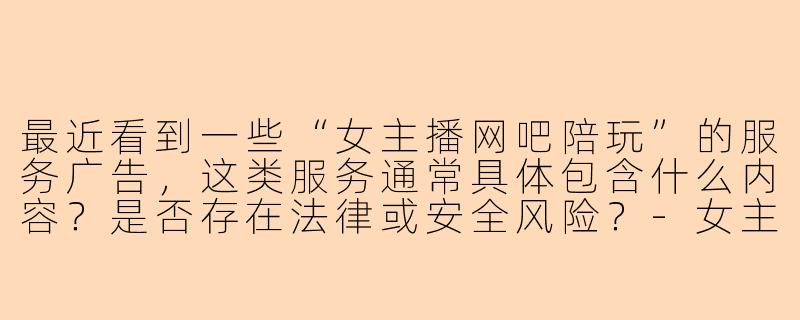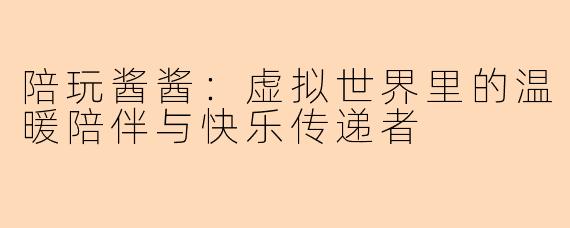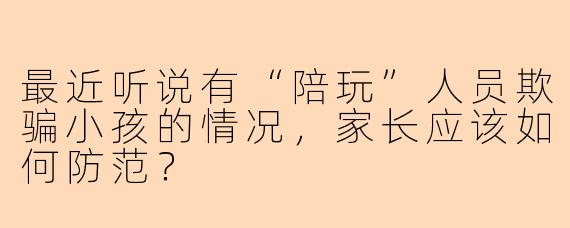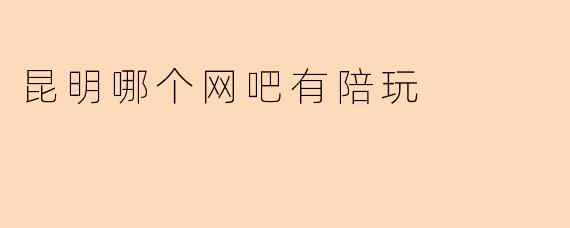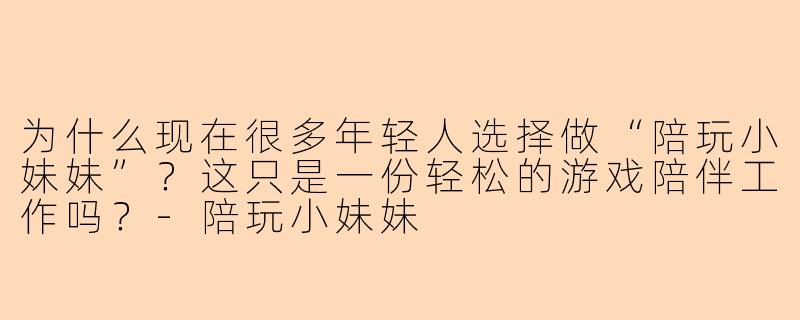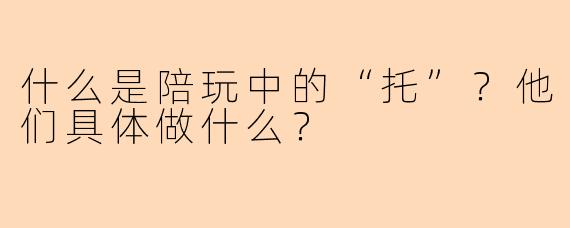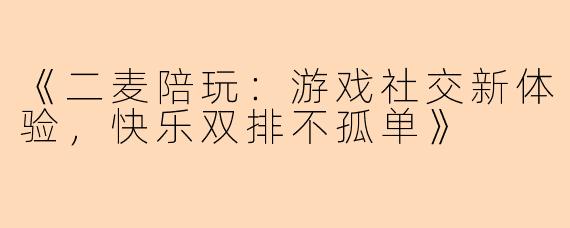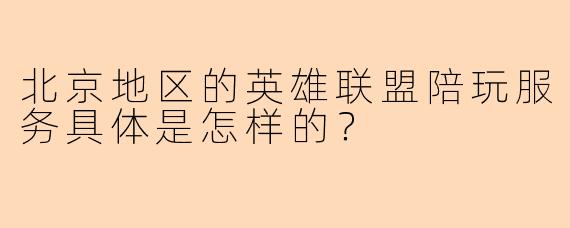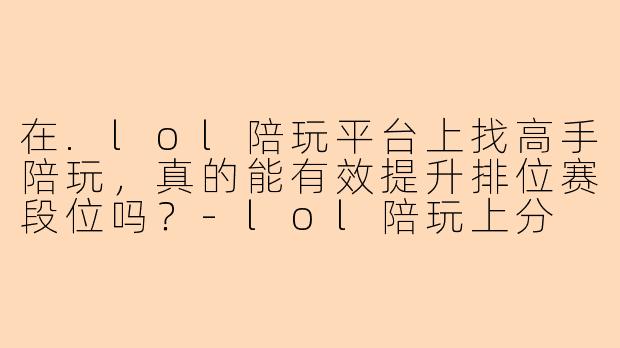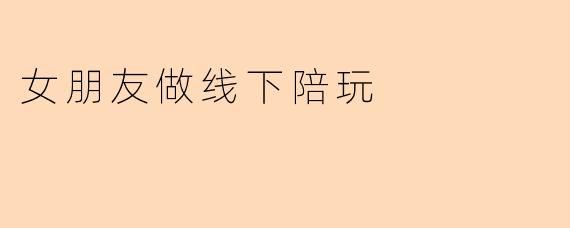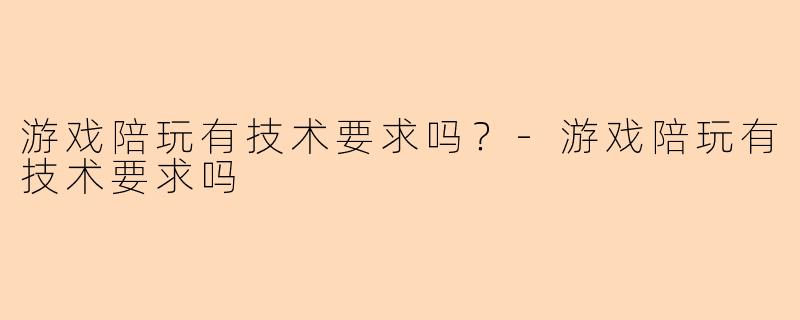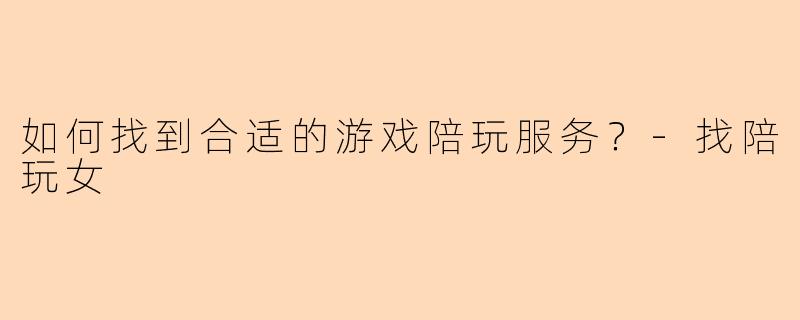凌晨三点,手机屏幕的光映亮她疲惫的脸。耳机里传来稚嫩的童声:“妈妈,这关怎么过呀?”她深吸一口气,让声音浸满蜂蜜般的甜腻:“宝宝别急,妈妈帮你看看哦。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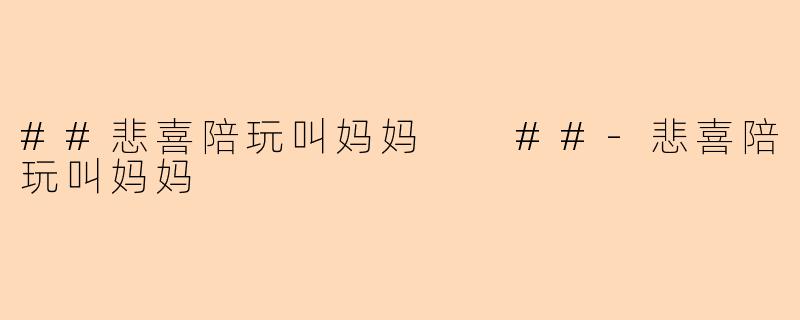
这是林晚今晚接的第七单“陪玩妈妈”。游戏界面上,五岁的小客户操纵着卡通小人跌跌撞撞。而在两千公里外的某座城市,真正的母亲或许正在沉睡,或许在加班,或许——像订单备注写的那样——“在国外出差,孩子想妈妈”。
“陪玩妈妈”,这个新兴职业悄然生长在游戏产业的缝隙里。客户是6-12岁的孩子,需求简单又复杂:陪打游戏,陪写作业,陪聊天,但必须全程称呼他们为“宝宝”,并自称“妈妈”。时薪从五十到五百不等,取决于“妈妈感”的逼真程度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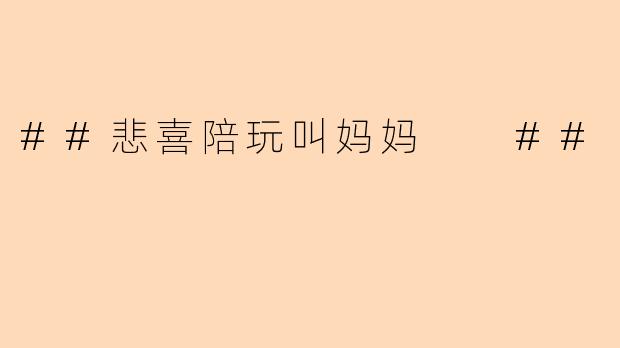
林晚的文件夹里存着十几个“妈妈剧本”。有温柔知性型:“宝宝真棒!妈妈为你骄傲”;有活泼可爱型:“哇!妈妈的小天才又过关啦”;还有严厉负责型:“作业写完才能玩游戏哦”。每个剧本都附带着对应的笑声频率——什么时候该轻笑,什么时候该开怀大笑,什么时候该带着宠溺的叹息。
她曾是幼师。三年前辞职时,园长惋惜地说:“孩子们最喜欢林老师了。”如今她的“孩子们”散落在全国各地,通过光纤和服务器与她相连。最长的客户跟了她两年半,从一年级陪到三年级。那孩子至今以为,自己的“手机妈妈”只是工作太忙。
“这算欺骗吗?”新入行的女孩曾这样问。林晚没有回答。她想起昨晚那个男孩,在游戏胜利后突然小声说:“妈妈,今天数学考了满分。真妈妈还没回微信,我先告诉你。”屏幕这头,她下意识地张开双臂,却只抱住了发烫的手机。
悲喜交加是这个职业最真实的写照。喜的是孩子们毫无保留的依赖——他们会分享第一颗掉落的乳牙,第一次独自睡觉的勇敢,甚至父亲新女友的香水味。悲的是每次下线时的“妈妈再见”,以及明知这种连接脆弱如蛛网。
有些陪玩妈妈会越界。同行小雅曾偷偷给一个孩子寄生日礼物,被家长投诉“骚扰”。公司明文规定:不准透露真实信息,不准线下联系,不准产生真实情感。“我们是云妈妈,”培训师说,“要像云一样,需要时出现,该散时就散。”
但情感怎能像云一样收放自如?林晚的收藏夹里存着孩子们偶然发来的照片:窗台上的蜗牛,歪扭的“妈妈我爱你”字条,拼好的乐高城堡。这些瞬间让她恍惚,仿佛自己真的在某个角落存在着,被需要着。
最近她接到一个特殊订单。十岁女孩指定要“和妈妈一起玩《我的世界》”。游戏里,女孩教她搭建记忆中的家:有秋千的院子,总是漏水的厨房,挂满照片的客厅。“这是我真正的家,”女孩说,“但妈妈走后,爸爸卖了它。”那一晚,她们在像素世界里重建了那座不存在的房子,直到晨曦微亮。
下线前,女孩突然问:“你会不会也突然消失?”林晚对着麦克风,轻轻哼起一首摇篮曲——那是她为自己早夭的女儿准备的,从未有机会唱出。耳机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,孩子睡着了。
这个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:“我们修补着别人的童年,却弄丢了自己的模样。”林晚的衣柜里,职业装和“妈妈装”泾渭分明。前者利落干练,后者总是柔软的棉麻质地,印着小花或卡通图案。化妆台上,口红分两类:正红色用于白天的职场,蜜桃色用于夜晚的“妈妈时间”。
她渐渐分不清哪种笑容更真实。在会议室里讲解方案时,她会突然冒出“宝宝真聪明”的语气;而对着孩子说“妈妈在呢”时,又带着项目管理的条理性。两个世界在灵魂深处交融,搅拌出新的、连她自己都陌生的人格。
午夜零点,新订单提示音响起。备注栏写着:“孩子妈妈刚去世,请温柔些。”林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,直到眼角弯出恰好的弧度。点击“接单”时,她瞥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——那个笑容既像母亲,又像小丑。
登录游戏,一个沉默的小人站在原地。她清了清嗓子,让声音裹上羽毛般的轻柔:
“宝宝,妈妈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