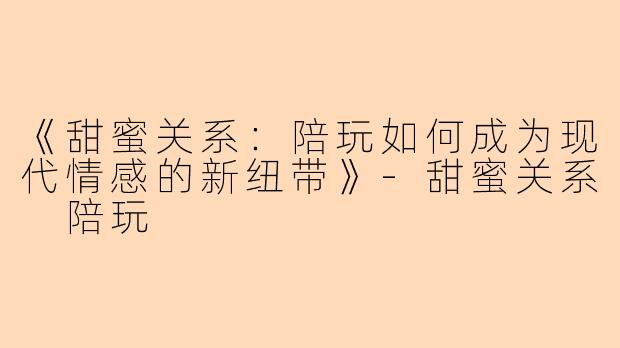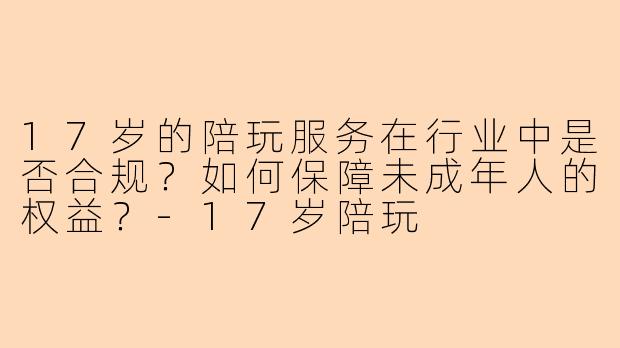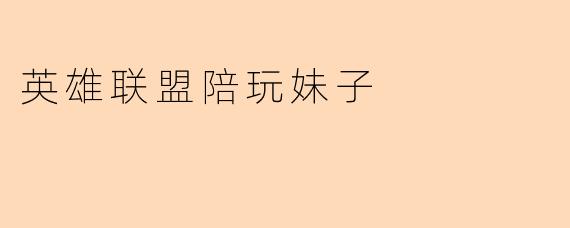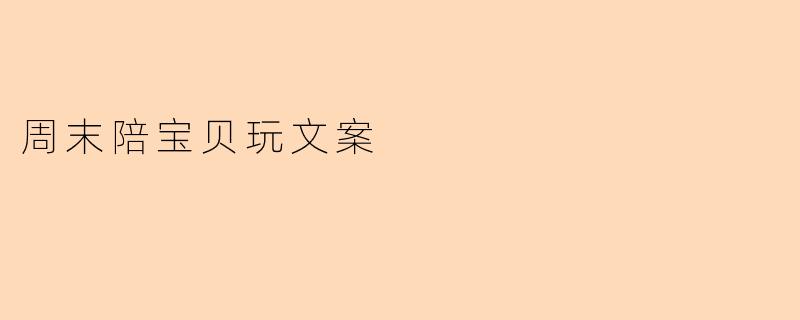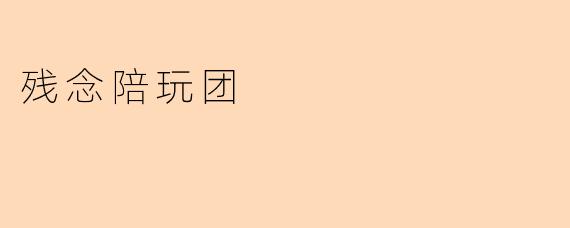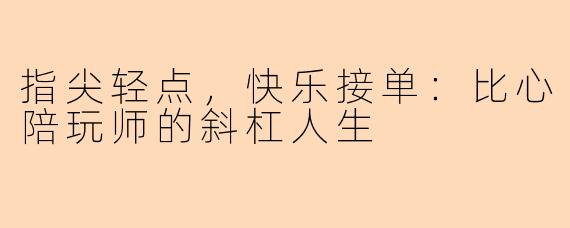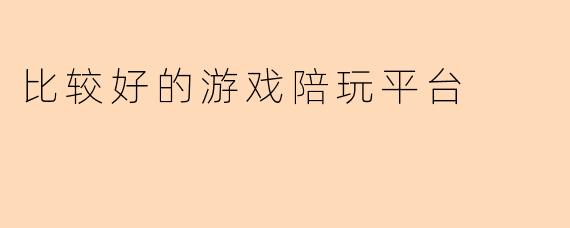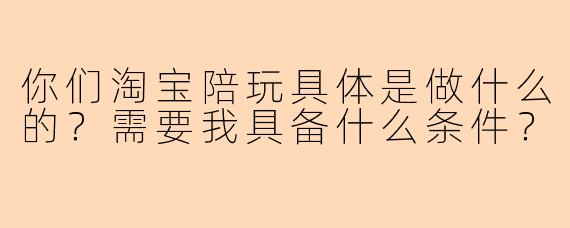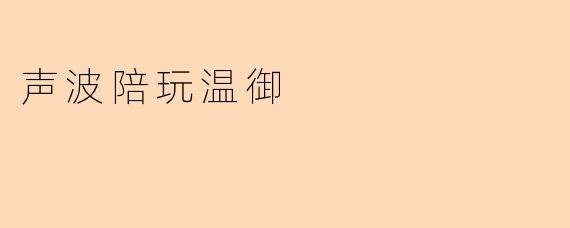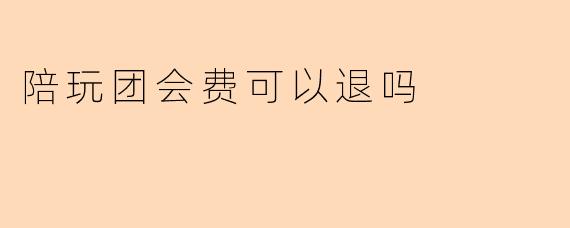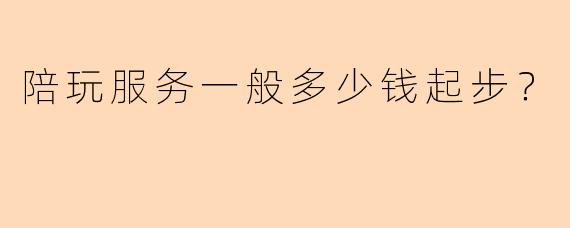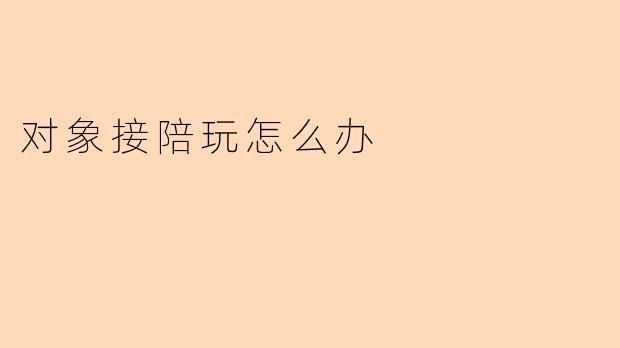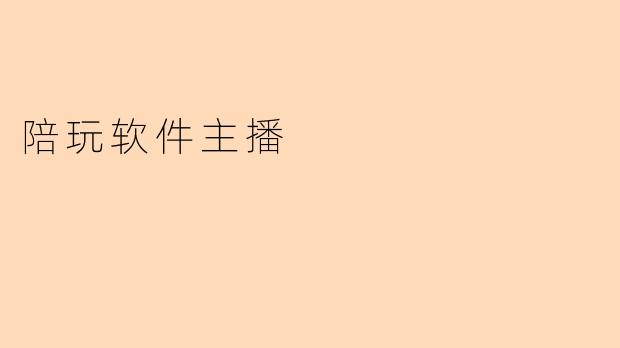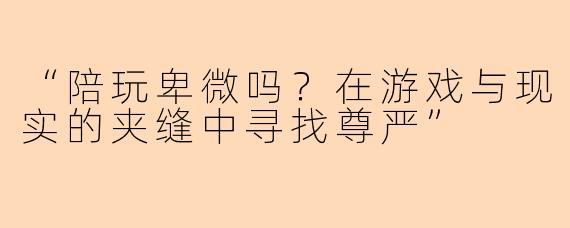在某个平行时空的互联网角落,“杨玉环陪玩”正悄然成为虚拟交易平台的热搜词条。当这位千年前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倾国佳人,被数字化为游戏陪玩界面中的一个选项,我们触碰到的不仅是商业逻辑对历史符号的挪用,更是一场关于记忆、消费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寓言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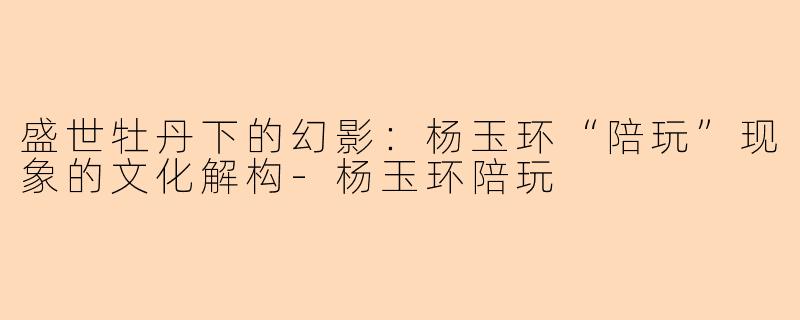
霓裳羽衣舞在手机屏幕里化作技能特效,华清池的温泉水凝成角色语音包里的气声呢喃。下单者购买的不仅是几十分钟的游戏陪伴,更是对盛唐气象的碎片化占有——在这里,历史被压缩为可量化的服务时长,文化符号沦为满足瞬时欢愉的消费道具。这种将历史人物“服务化”的叙事,折射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历史认知的扁平化危机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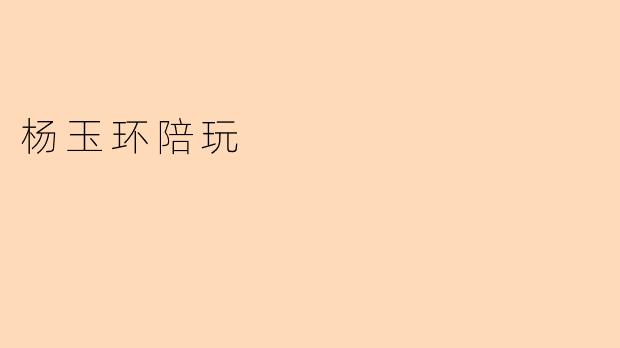
考证《旧唐书》与《长恨歌》的笔墨,真实的杨玉环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,是盛唐由盛转衰的隐喻性符号。她承载着胡汉交融的文化特质,代表着开元盛世最后的艺术辉煌。而当算法将她的形象简化为“国服中单”“声甜会撩”的标签,我们失去的正是历史人物身上的复杂性与悲剧厚度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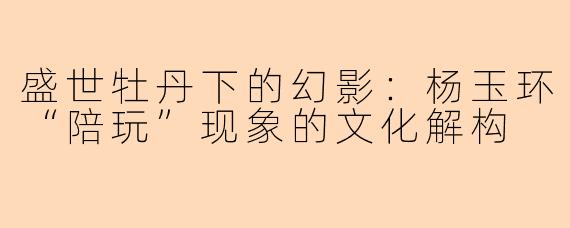
值得深思的是,这种文化消费背后涌动着的,实则是当代人对盛唐气象的集体乡愁。在虚拟世界里重构与历史名人的联结,本质上是对文化根脉的无意识追寻。只是当沉香亭北的阑干被像素化,当《霓裳羽衣曲》变成游戏背景音,这种文化慰藉是否正滑向历史虚无的深渊?
更有甚者,女性历史人物在数字时代的再创作往往陷入性别凝视的窠臼。无论是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的文学想象,还是当下陪玩市场中的角色扮演,杨玉环始终被禁锢在他者建构的欲望叙事中。这种千年不变的符号化命运,比任何技术异化都更值得警醒。
当我们解构“杨玉环陪玩”这个文化样本,最终需要追问的是:在数字消费的狂欢中,我们究竟是在激活历史,还是在消解历史?当下一代年轻人通过游戏角色认识杨玉环,他们失去的将不仅是真实的历史维度,更是与文明传统对话的能力。或许该让数字时代的牡丹重新扎根于历史的土壤,让被消费主义解构的文化符号,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更有尊严的重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