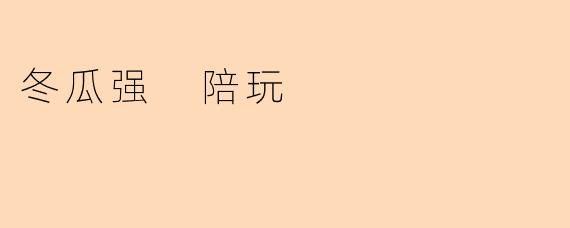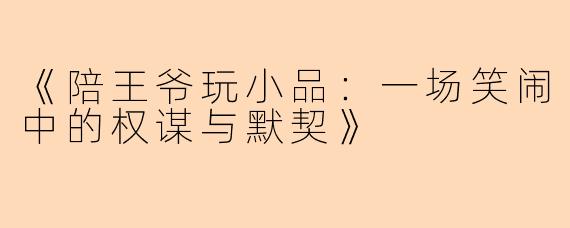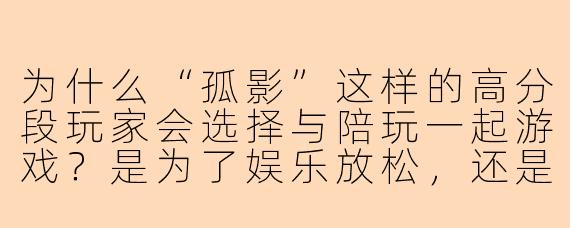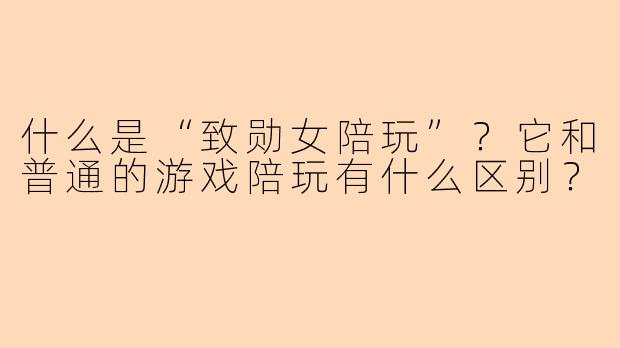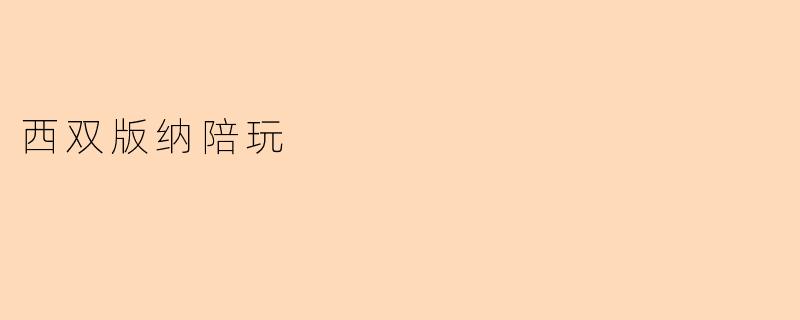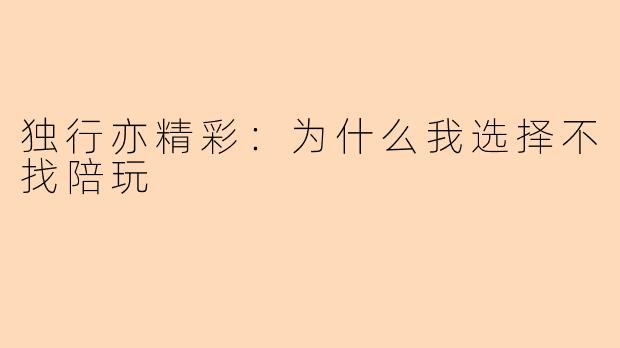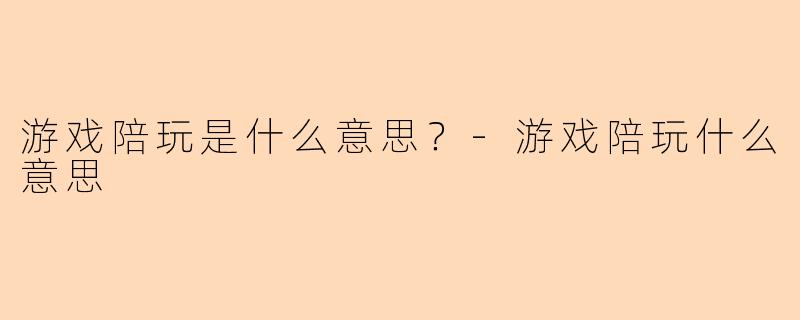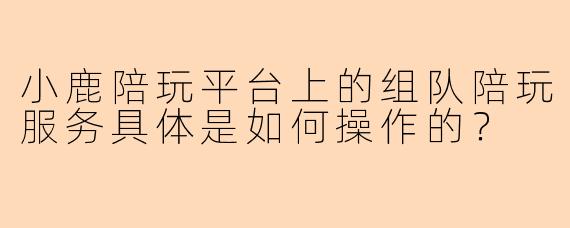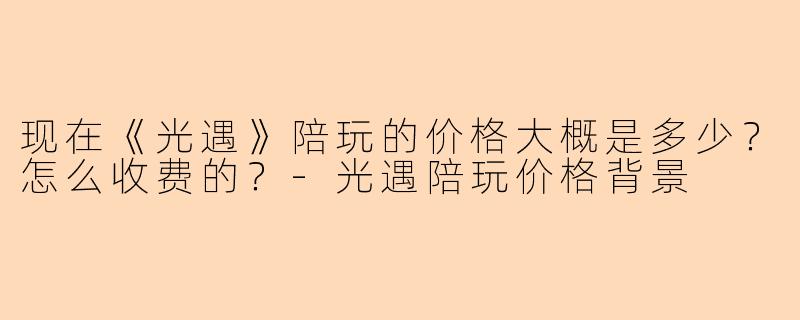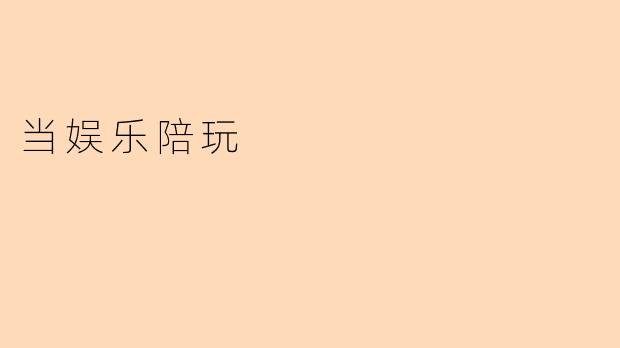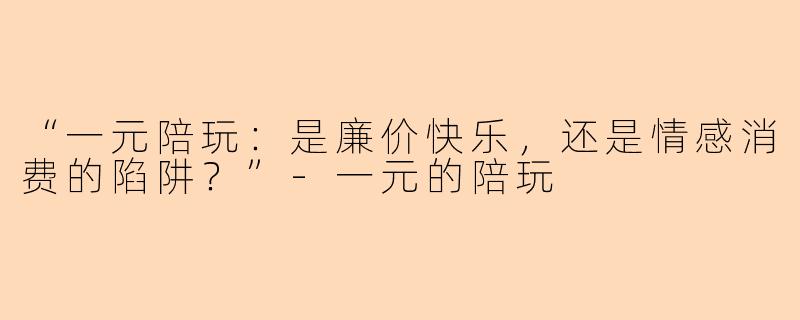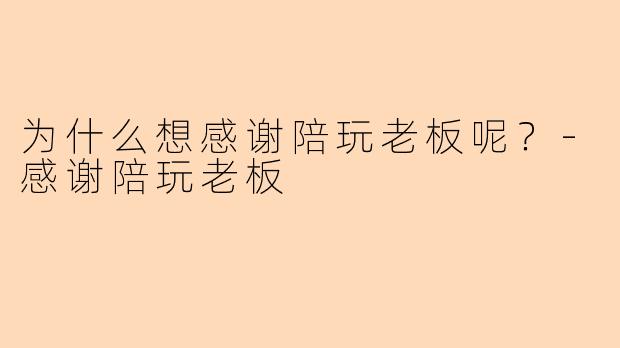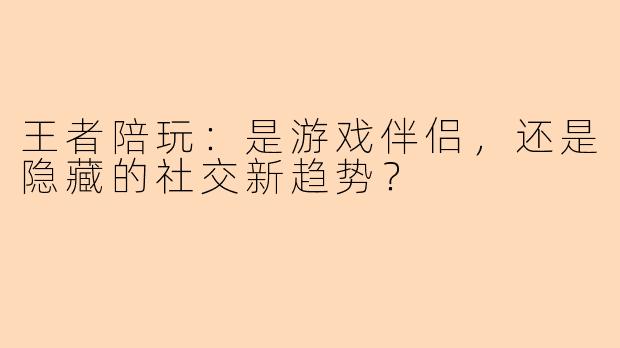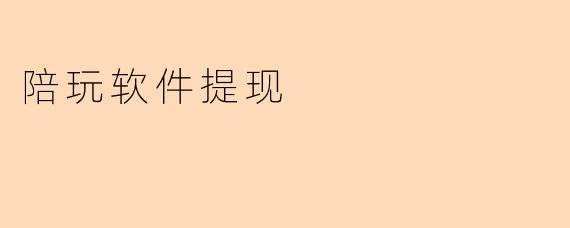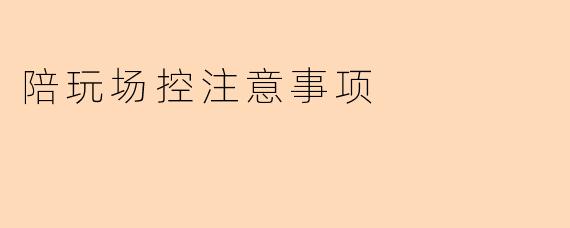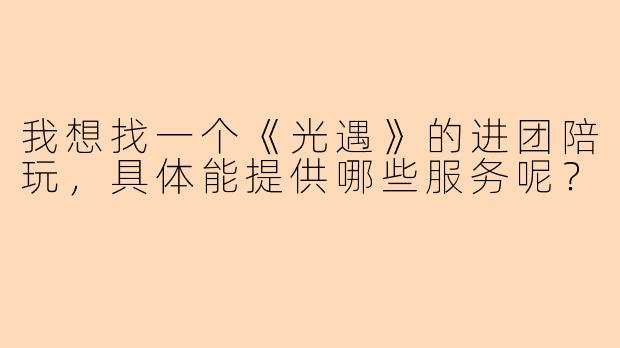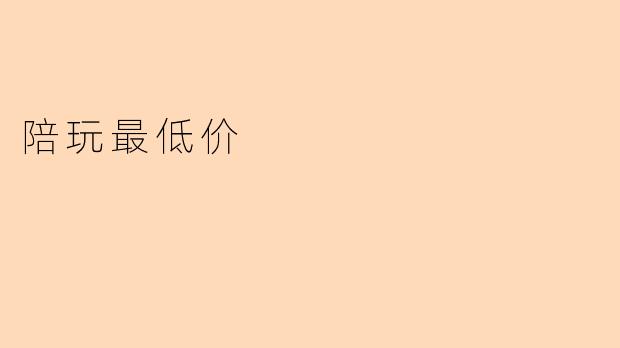深夜十一点,小陈的耳机里传来客户的催促:“再打一局,我马上晋级了。”他揉了揉发酸的手腕,熟练地点开匹配界面。这是小陈本周接的第20单“陪玩”业务——通过游戏平台接单,陪客户打游戏,按小时收费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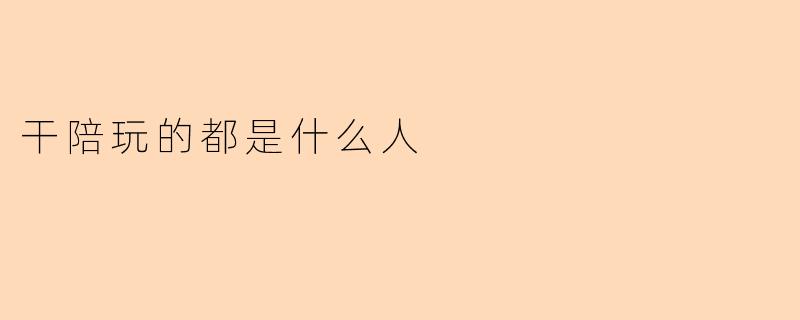
像小陈这样的“陪玩师”,正成为新兴数字职业中的一员。他们大多年轻、擅长游戏,却不止靠技术吃饭。有人称他们是“虚拟世界的情感摆渡人”——在提供游戏陪伴的同时,悄然承载着都市人的孤独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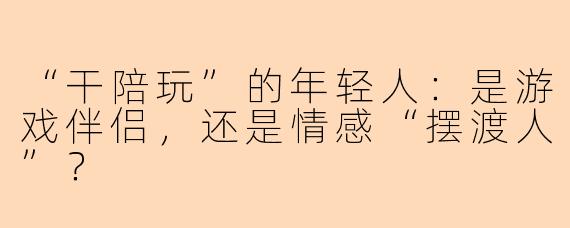
“技术流”与“氛围组”:陪玩的两副面孔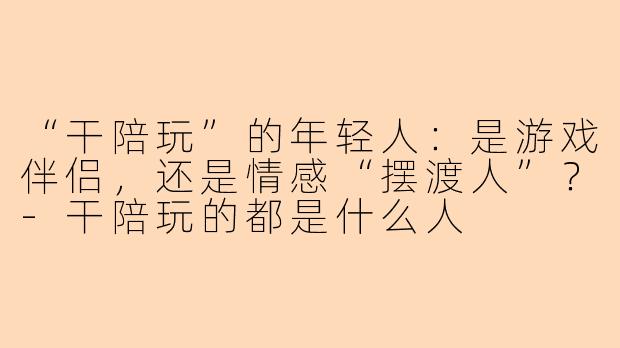
陪玩群体主要分为两类:一类是“技术流”,以高段位、强操作吸引追求胜利的玩家;另一类是“氛围组”,擅长沟通、能调节气氛,甚至用声音或幽默感留住客户。
22岁的女生小雨属于后者。“有些客户找陪玩,其实只想有人说说话,”她曾在凌晨听一位创业者讲述公司困境,也安慰过因失恋连输五局的大学生,“游戏只是载体,他们需要的是被倾听的感觉。”
“时薪过千”与“隐形压力”
行业顶层的陪玩收入惊人。某平台明星陪玩时薪可达千元,但背后是严苛的竞争:每周考核胜率、客户评分,甚至要学习心理学话术。
然而光鲜之下藏着隐痛。25岁的阿默展示了他的工作时间表:下午1点到凌晨4点在线,吃饭不敢离开超过20分钟。“这行吃青春饭,客户今天叫你‘大神’,明天可能就因为输游戏投诉你。”
边缘生存与身份焦虑
尽管市场规模已超百亿,陪玩师仍面临职业认同困境。有人被家人误解为“不务正业”,有人在相亲时隐瞒职业。更现实的是社保缺失、收入波动、职业寿命短暂等问题。
心理学教授李帆认为:“陪玩本质是‘注意力经济’的产物,折射出当代人既渴望连接又害怕真实接触的矛盾。这个群体就像数字时代的‘手艺人’,用虚拟技能换取报酬,却尚未获得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感。”
凌晨三点,小陈终于结束今天最后一单。客户发来消息:“下次还找你。”他放下发烫的手机,窗外只有零星灯火。在这个永不眠的赛博世界里,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人,用键盘和麦克风构筑着他人短暂的快乐,也在虚拟陪伴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