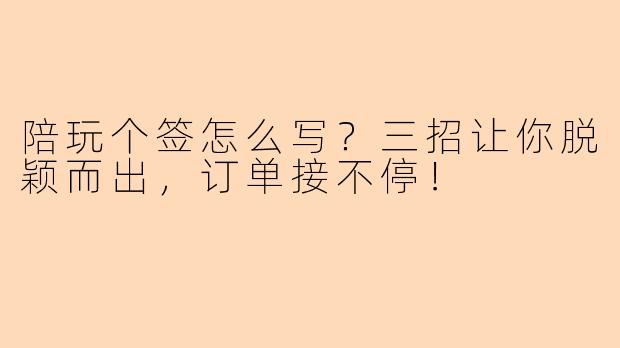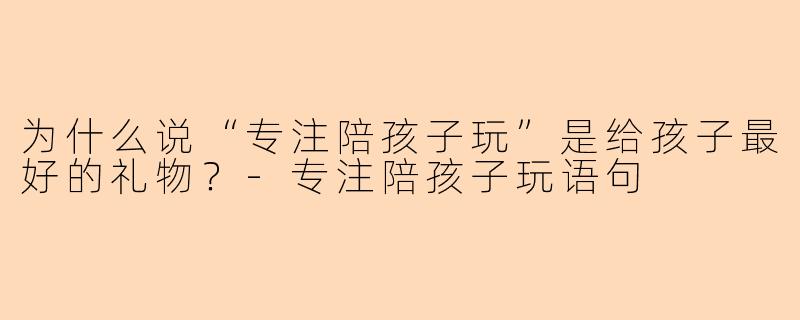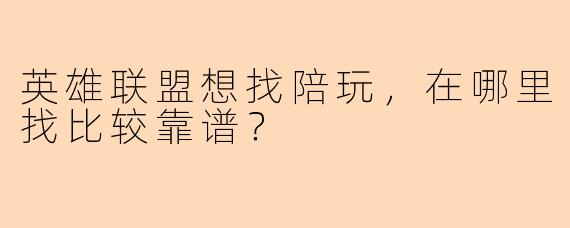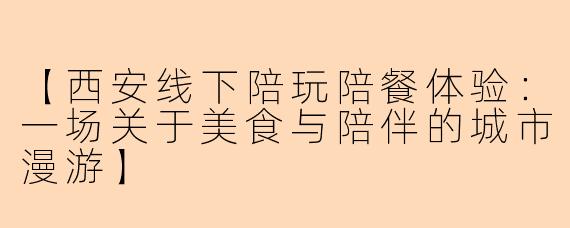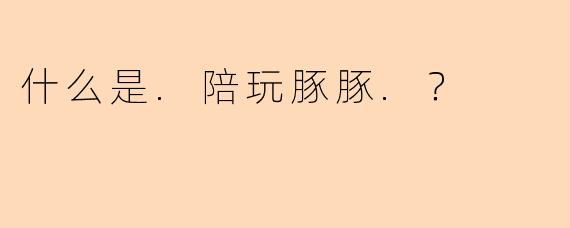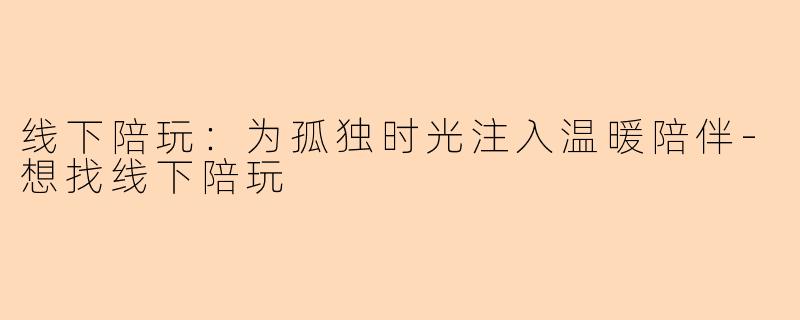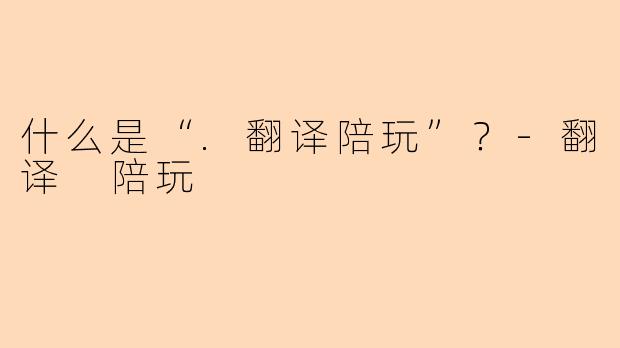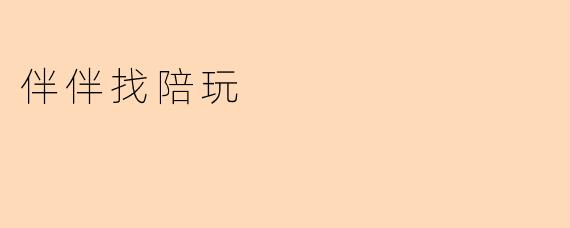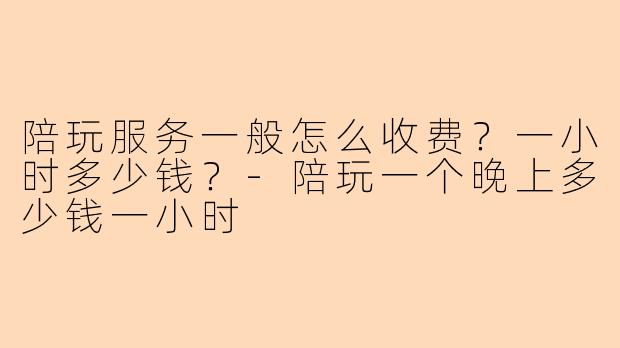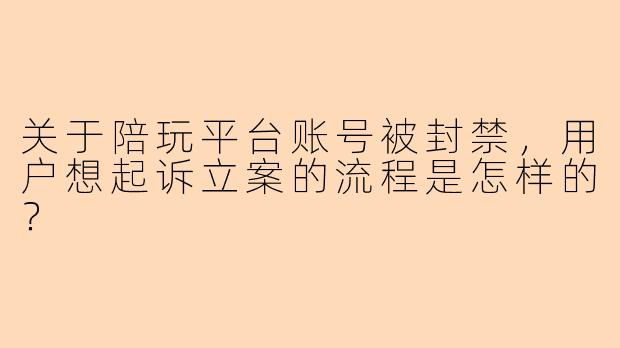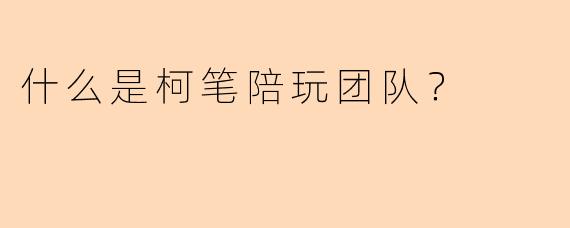屏幕右下角的游戏图标已经三天没有亮起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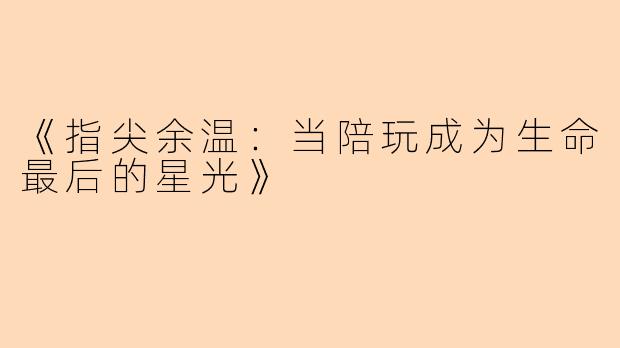
林薇的聊天窗口停留在最后一句:“明天老时间,带我打最后那个副本呀。”后面跟着她常用的猫咪表情包。她总是这样,明明已是癌症晚期,却把每次化疗称为“副本挑战”。我是她的陪玩,时薪八十,陪她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走了九个月。
最初接单时系统提示“客户有特殊需求”。见面语音里她的声音很轻:“医生说我大概还有一年,我想完整地玩通这个游戏。”于是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游戏计划,从新手村到终极副本,像完成某种生命倒计时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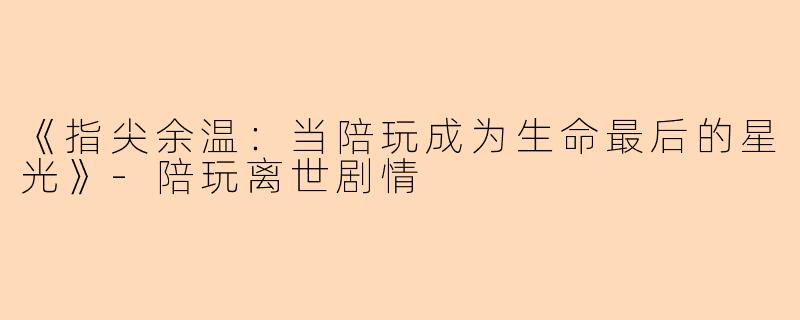
她操作很慢,化疗后常常突然掉线。有次在雪山地图,她的人物突然不动了,耳机里传来压抑的呕吐声。我静静等着,二十分钟后她回来,声音虚弱:“继续吧,雪景真美。”那天我们什么任务都没做,就在游戏里看了一小时虚拟雪景。
第七个月,她开始委托我记录游戏细节。“要是我妹妹以后想玩,你可以教她。”她有个十岁的妹妹,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,很少来看她。游戏成了她的树洞,她说在这里,疼痛会变成血条可见的东西,打倒了就能继续前进。
最后那个副本,我们打了三周。她的反应速度明显下降,但坚持不用简单模式。“如果这是最后一个关卡,”她说,“我想真正地通关。”通关那晚,她在语音里轻轻笑了,那是我认识她以来最清脆的笑声。
昨天她妹妹用她的账号发来消息:“姐姐今早走了。她说谢谢你陪她打完所有关卡。”随后转来一笔额外的费用,备注写着“最后的陪玩费”。
我点开游戏,登录我们共同创建的公会。仓库里整整齐齐放着我们一起收集的所有装备,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件她最爱的白色婚纱外观——这是游戏里没有任何属性的装饰品,她说像真正的婚纱。
屏幕突然飘起游戏里的樱花雨,这是她设置的定时邮件:“当你看到这个,我大概已经通关人生这个最难副本啦。别难过,你陪我的这些时间,让我觉得最后这段路不是一个人在走。账号留给你,替我看看以后的新版本吧。”
窗外夜色渐深,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。我操纵着她的人物走到我们常看日出的悬崖边,游戏里的朝阳正在升起。突然明白,这九个月不是我陪她玩游戏,而是她陪我上了一堂关于生命与告别的课。在虚拟世界的某个角落,那个角色会永远站着,而有些陪伴,即使一方缺席,依然在记忆里持续发热。
陪玩这份工作,原来不只是消磨时间。有时候,我们陪别人走过的最后一段路,会成为彼此生命里永不掉线的星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