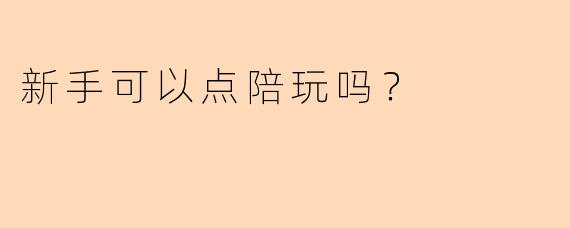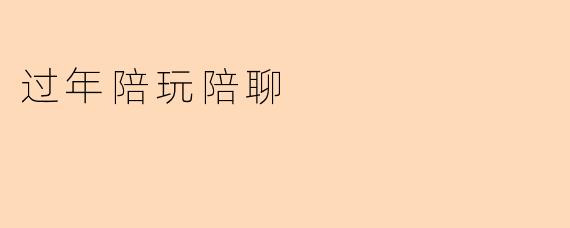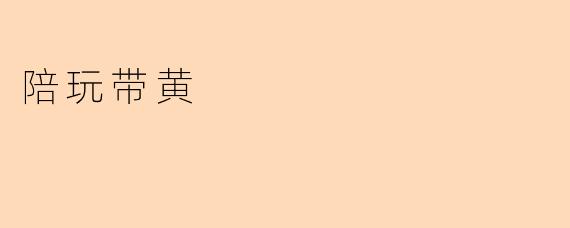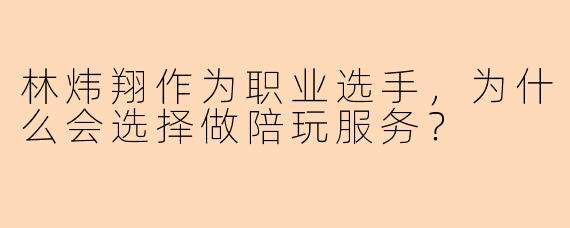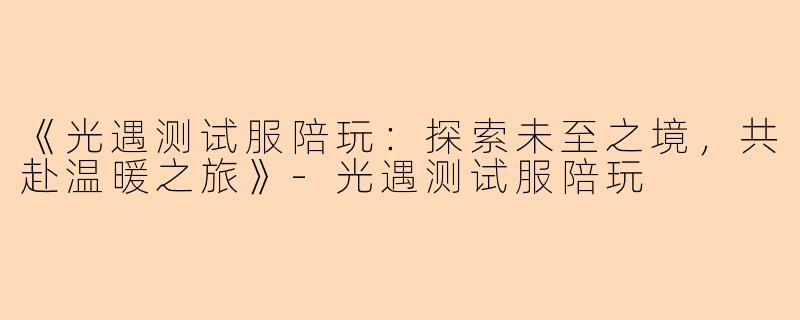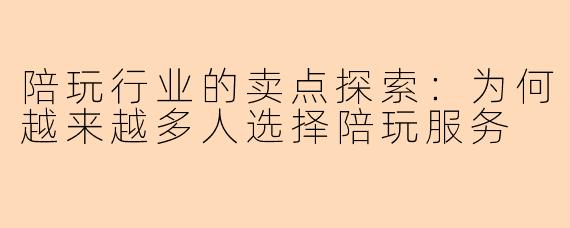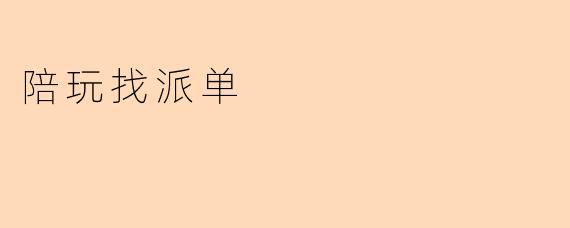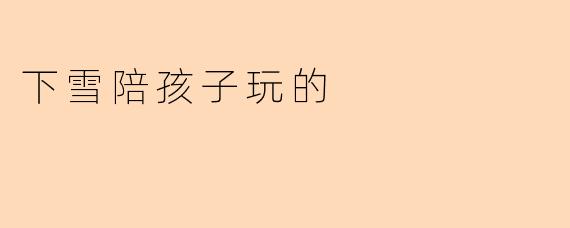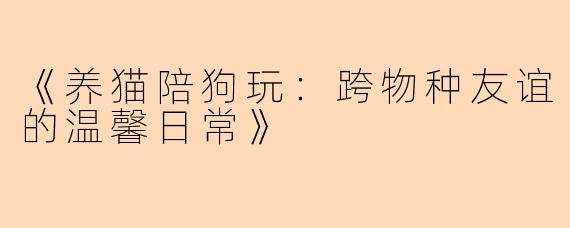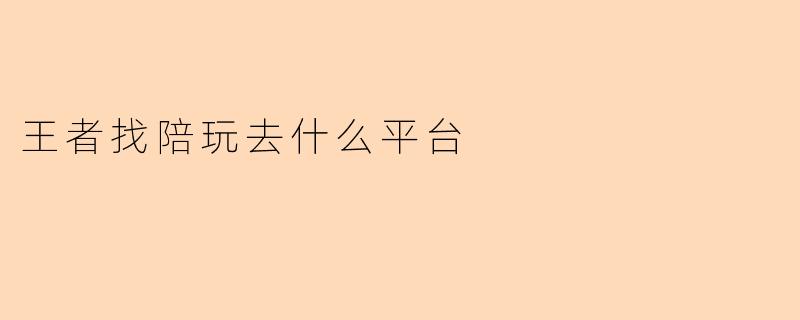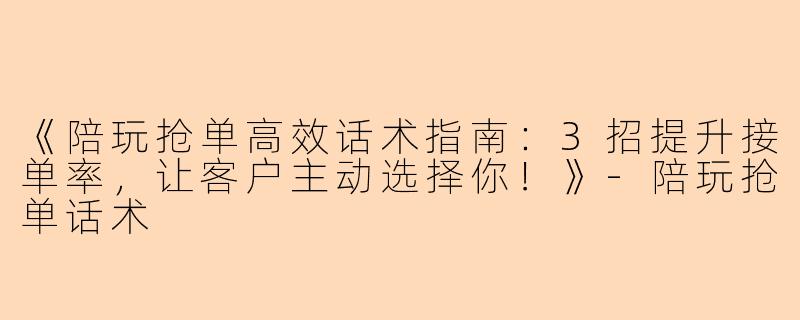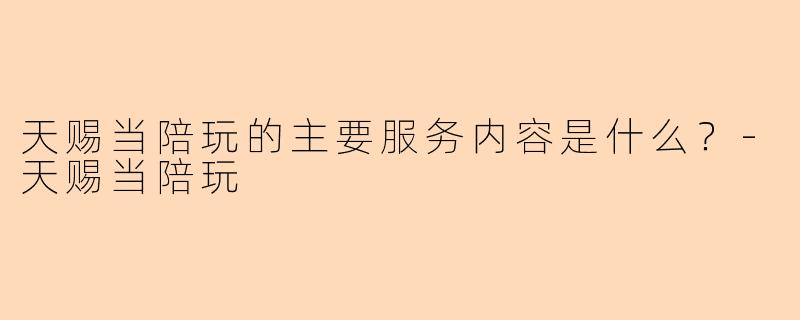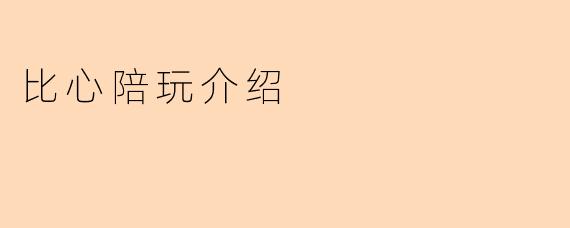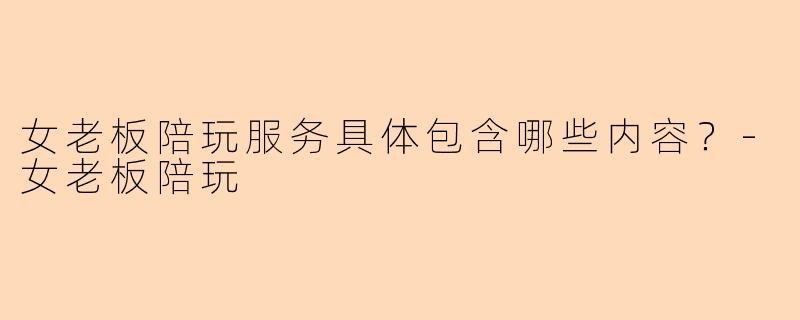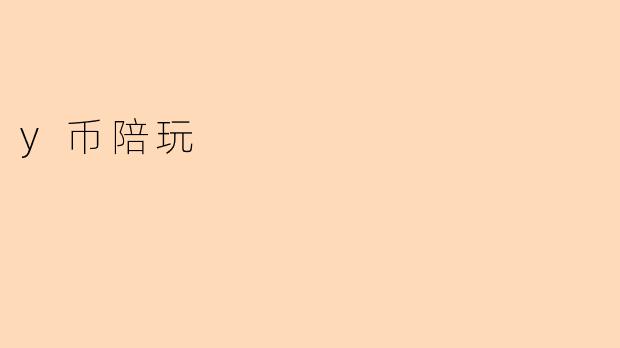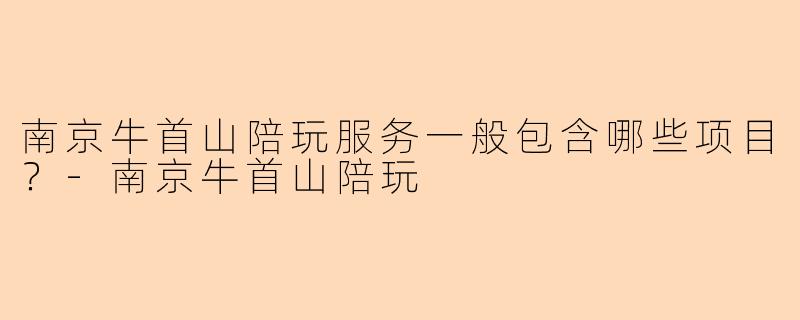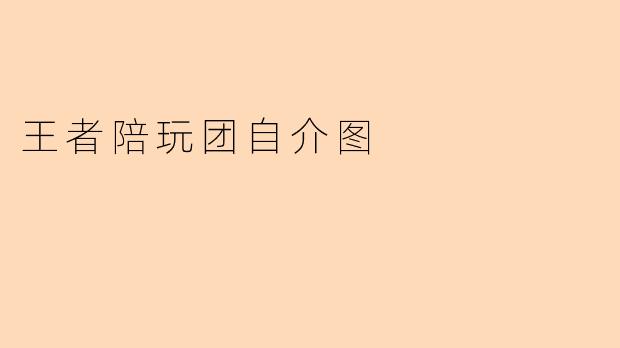深夜十一点,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林澈疲惫的脸。耳机里传来女孩轻快的笑声:“哥哥这波操作好厉害呀!”他熟练地调整语气,让声音听起来温暖又充满活力,尽管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六个小时。在网络的另一端,那位叫“薇薇”的客户刚刚支付了每小时一百五十元的费用,购买他的游戏技巧、声音陪伴,以及一份按分钟计费的“情绪价值”。
这就是“陪玩”——一个在游戏产业缝隙中蓬勃生长的新兴职业。它远不止是“陪着玩游戏”那么简单,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感消费与社交租赁。雇主购买服务,寻求的是技术带飞上的胜利快感,更是排遣孤独的心灵慰藉;陪玩师出售时间,交换的不仅是报酬,还有在虚拟世界中扮演另一个“完美自己”的机会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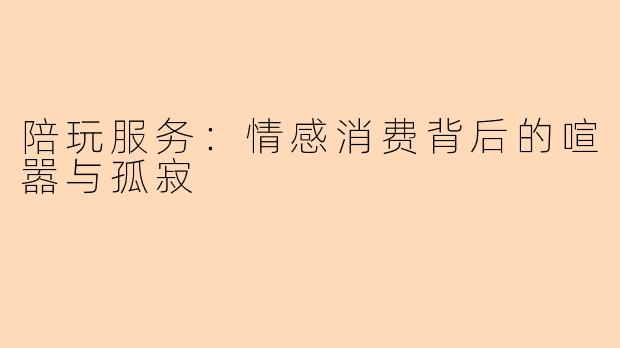
行业的兴起,根植于现代都市青年日益庞大的孤独感与情感缺口。在高强度、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,许多年轻人被困于“996”的工作模式和“社恐”的线下社交中。他们的社交需求被极大地挤压,转而投向网络世界寻求低成本、高效率的情感补偿。一个随时可以下单、随时可以结束、无需负复杂责任的临时伙伴,成了最具吸引力的商品。陪玩平台精准地捕捉并资本化了这种需求,将“陪伴”细化成各种标签:技术陪、娱乐陪、聊天哄睡……仿佛一份情感超市的商品目录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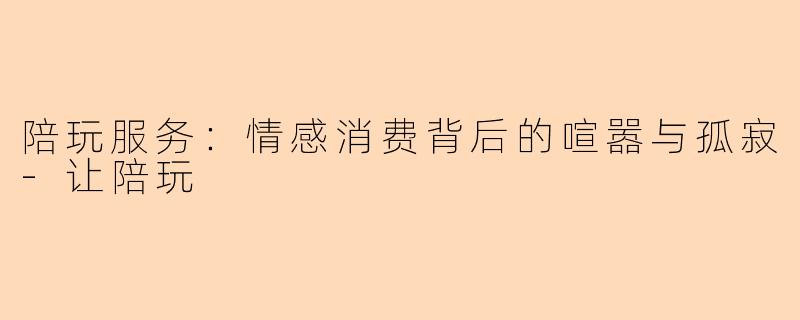
然而,光鲜的交易背后,是双方都无法回避的情感劳役与身份困惑。对于陪玩师而言,这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情绪表演。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需求,随时切换“大神”、“暖男”、“知心姐姐”或“搞笑玩伴”的人格面具。林澈的文档里记录着不同客户的喜好:“王老板,35岁,喜欢被夸技术好,爱聊职场压力”;“草莓喵,学生,需要情绪安抚,喜欢甜宠剧话题”。真实的情绪和感受被小心翼翼地收起,展示出来的,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打磨的“服务型人格”。这种长期的情感透支,让他们在摘下耳机后,常常陷入更深的虚无和疲惫,甚至模糊了虚拟服务与真实自我的边界。
而对于购买服务的客户而言,这种关系也脆弱得如同泡沫。短暂的欢愉之后,是更深的清醒。金钱交换来的热情和关注,终究带有表演的性质。当订单结束,关系也随之冻结,下一次连接,可能需要再次付费才能“激活”。这种建立在消费之上的脆弱联结,有时非但不能填补孤独,反而会映照出内心深处更大的空洞。
平台与资本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。它们通过算法匹配、营销话术,将这种情感消费包装成一种时尚、轻松的生活方式,刻意淡化其间的复杂性和可能的风险。纠纷、欺骗甚至更严重的安全问题,也时常在监管的灰色地带中滋生。
陪玩,这面时代的镜子,映照出的是一代人的喧嚣与孤寂。我们一边渴望真实的连接,一边却又依赖金钱去购买一份即时的、可丢弃的慰藉。它无疑为许多人提供了暂时的情绪出口和灵活的生计,但其背后的情感异化与伦理困境,却值得我们更深沉的思考:当陪伴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,我们最终得到的,是缓解了孤独,还是更深地典当了自己真实的情感能力?在这场大型的线上情感实验中,没有谁是完全的赢家。